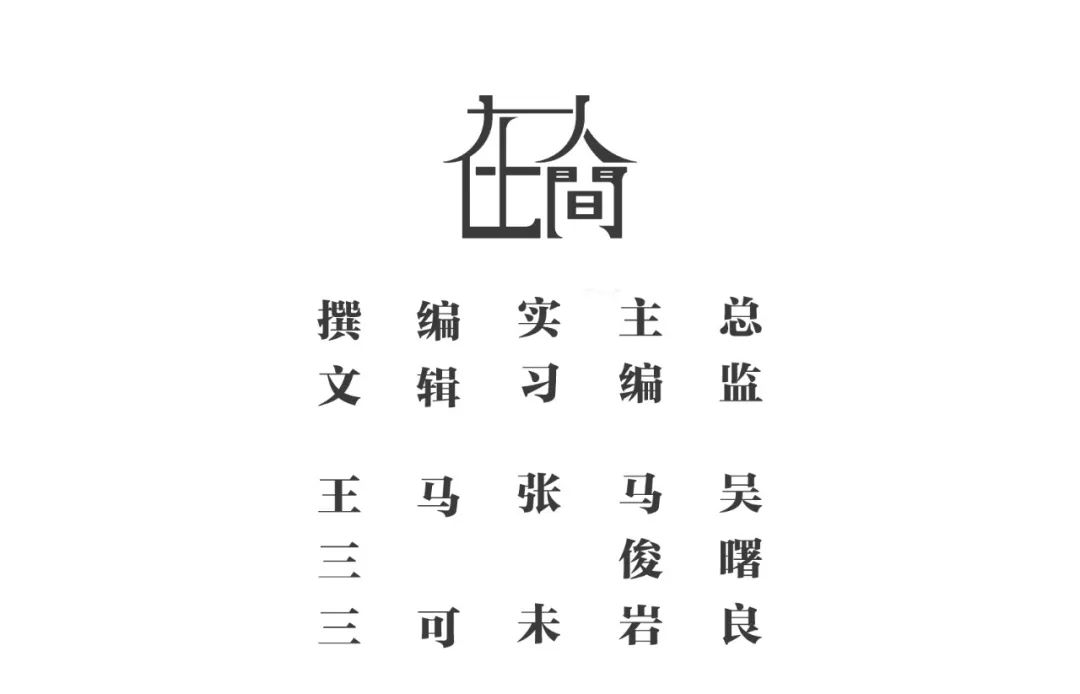“他放飞自我了”,小岱妈妈还是第一次看见儿子随着音乐,用脚自由地打拍子。他带着一脸笑意,浑身放松,沉浸在欢快的节奏中。小岱今年18岁,是深圳爱特乐团的陶笛手。“爱特”是孤独症“Autism”的谐音,也有“爱这群特殊小孩”的深意。乐团由6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到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从此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乐团成立的时候,我看到了曙光。我特别希望乐团能够生存下去,让孩子们有一个去处”,一位孤独症家长说。
今年乐团正好迎来十周年,目前有13位成员,全部是孤独症人士,最小的16岁,最大的39岁。在4月2日抖音平台直播的「拾」光音乐会舞台上,他们每个人都如星星一般闪耀。这些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融入普通学校和社会都曾困难重重。音乐给了他们希望。

四处求医半年后,小岱妈妈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儿子是个孤独症这个冰冷现实。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岱按学区被分到深圳一所新建的普通小学,全校上上下下只有他一个特殊儿童,年轻的老师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在普小,小岱从未开心过。小岱妈妈申请陪读,也历经一番坎坷。班主任不同意,副校长虽表同意,却强调“要任课老师没意见”。有的老师允许她进教室,她就端一张小矮凳坐在角落里,极力隐身;有的老师不允许,她只得站在后门窗外张望。“我亲眼看见,他被排斥”,讲到这,小岱妈妈哽咽了。小岱有语言障碍,反应慢,看起来文静,没什么大动作,但琐碎的小动作还是让人感受得出他的不一样。有一次,小岱妈妈接孩子放学,遇到同班一个男同学。“他跟妈妈一起,上来跟我打招呼,我让小岱也跟他打招呼。孩子妈妈站在原地,斜着眼上下打量小岱,很不友好。”小岱妈妈回忆道,“我拉着儿子就走了” 。还有一次,已经上三年级的小岱去洗手间,“就在班隔壁,我很放心,他从不走错”,小岱妈妈在教室里,等了很长时间,还没见儿子回来。“问一个小女孩,她说‘阿姨快去看看吧’。”原来小岱被拽到女厕所去了,还被一群女孩推搡着。“我觉得很无力,孩子没有错,那些女孩主观上也没恶意。小岱确实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压力。”到后来,一遇到有公开课之类的,小岱妈妈总是主动请假。安静的小岱,在哪里都没什么存在感,几乎也没朋友。班级里,同学们经常议论他——打一下没反应,像个傻子……乐团里年龄最大的贝贝,30年前读书的时候,学校老师连孤独症是什么也不清楚。“贝贝上学,是令家长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他妈妈孙莉莉说。8岁,贝贝从国企办的幼儿园升入小学。去学校不到一天,老师反映有家长投诉贝贝影响班里其他孩子上课,让接回家。“我们很急,两个人都要工作,学龄到了不上学怎么办?”后来想尽办法找了五六所小学,也是一天不到就退回来。孙莉莉只得把孩子送去了杭州特殊学校。不到一个星期,又被叫到学校,“还是不行,说贝贝推小孩” 。贝贝不懂表达,他想跟小朋友示好,却掌握不了正确的社交方法。连特殊学校也不收,“真是走投无路了”。实在没办法,夫妻俩将贝贝领回家,每月花一半的家庭月工资,请退休老师上门教贝贝文化课知识。《2021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蓝皮书》透露:全国0至18岁孤独症儿童保守估计300万人。很多孩子都如小岱和贝贝一样经历了就学融合困境。很多孤独症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比如,很多学生往往都被安排在班级最角落的一个座位,以防止他们“打扰”其他同学;课业教师并不关注特殊需要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因为随班就读学生不纳入教师和学校的绩效考核);再比如,很多校园活动他们都被建议不参加,担心他们“不安全”。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项目人员姜正红曾经听有位老师形象地指出,“你看到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走进了同一所学校的校门,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直有一个看不见的墙隔离着他与其他孩子。”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把普通教育机构招收特殊学生随班就读作为发展特殊教育的一项政策。2017年,融合教育首次写进《残疾人教育条例》,其中第58条规定:融合教育是指将对残疾学生的教育最大程度地融入普通教育。姜正红认为,对孤独症孩子而言,“融合教育的重点是让他们如何像同龄孩子一样,这孩子能够在人堆儿里待着,待的时间越长,和其他孩子接触越多,这个融合教育就越成功。同龄人之间就是互动、学习和模仿,这种环境是父母给不了的,也不是特殊学校能给他的,融合学校的环境才能给他”。但中国融合教育还在发展初期,很多随班就读的孤独症儿童难以真正融入校园生活。这种困境来自学校、家长、同学等多个层面。普通学校老师本身没有特教经验,不知道孤独症孩子会出现哪些行为,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老师只能求助家长,严重的情况下,只能劝退。家长们对孤独症孩子有所顾忌,总是不自觉地把他们归为坏孩子,不希望自己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受到干扰和影响,曾出现过家长联名要求孤独症孩子退学的情况,很多孩子因此辍学,或转入特殊教育学校。另外,被同龄人误解、歧视、取笑,几乎是每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普通学校都要面对的困境,严重的还会被霸凌。小岱在普通学校遭遇种种歧视,他妈妈发现融合教育这条路走不通,只得让孩子退出,进入特殊教育学校。为了儿子的成长,小岱妈妈让他从10岁开始接触各种乐器,最早学的是陶笛。起初,妈妈跟儿子一起学,一起登台,算是二重奏,“怕他吹得平淡,给节目增点色” 。小岱学到中级后,妈妈跟不上进度,只能在一旁记录知识点,或播放标准示范曲。孤独症孩子兴趣特别狭窄,学艺术是家长出于私心,希望将他们从封闭的世界里拉出来。乐团每个孩子走上音乐的道路,各不相同。贝贝是乐团年龄最大的成员,钢琴十级,还会弹吉他和双排键。乐团成立之前,他已在深圳小有名气。在杭州特殊学校被拒后,孙莉莉带全家到了深圳,经人介绍把孩子送到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条件和环境很好,也肯收贝贝” 。到了19岁,贝贝成年了,不能继续待在特殊学校了。那时国企改制,孙莉莉主动下岗,从此24小时陪伴着儿子。贝贝20岁那年,一家三口逛超市,父亲寿虹看到一架90元的电子琴,当玩具买回了家。寿虹正摆弄琴键时,贝贝突然开口道:“爸爸不弹贝贝弹。”第一次听孩子主动要求,孙莉莉很开心,“找到孩子兴趣点了”。第二天,她带着儿子去了琴行。此后的一个月,孙莉莉天天带着儿子去练琴。贝贝学琴,她一直陪在旁边,记下老师讲的重点,回家再用贝贝容易懂的语言转述给他。光是认五线谱,孙莉莉便用白纸描上谱子,反复给儿子灌输,“哆”唱什么调怎么写,“咪”唱什么调又怎么写……贝贝花了两星期,死记硬背下来。学琴极其枯燥,贝贝也厌倦过。每当不想练时,他就躲进厕所里逃避,一两个小时不出来,孙莉莉只能在外面哄。她小心呵护着儿子的热情,物质上奖励巧克力;精神上鼓励。贝贝喜欢“听表扬、听掌声”,孙莉莉便带着儿子四处参加公益演出和比赛,引起了不少本地媒体注意,“起码有一部分关注到孤独症群体”,这点令她颇感欣慰。贝贝以前出门经常遭白眼,1.86米的他走起路来还蹦蹦跳跳,吓到过不少住户。搭电梯时,一些女孩子看到他,立马掉头出去,“不跟我们坐一架,我也挺伤心的” 。媒体曝光多了,小区居民对贝贝也改观了。在路上遇见,总是鼓励贝贝说“你好棒啊”“你要加油啊”。电梯里,小朋友看到贝贝,也会说“贝贝哥哥,你好棒”。“贝贝的事让很多喜欢音乐的孤独症孩子家长看到了希望”,孙莉莉说。她萌发了一个念头——把孩子们组织起来,让家长们抱团取暖,也让更多人接受和尊重孤独症孩子。2013年10月,深圳爱特乐团成立,成为国内首个全部由孤独症人士组建的音乐团体。最初的经费来源,是拍卖贝贝的画作和爱心捐款。成团之初,没老师肯教。好在教贝贝钢琴的陈老师愿意先帮忙将乐团组织起来,没排练场,就在贝贝家练。老师也头疼,孩子们根本不听指挥。以前孩子们独自在家练习,成团后要互相配合,对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们来说,只能一步步来。第一次演出,家长们找到南山村一个露天水泥搭的舞台。刚好是夏天,每个孩子穿得端正,白衬衣、蓝裤子和皮鞋。他们在台上表演,志愿者们在台下拿着捐款箱募捐。“当时我们演出水平一般,也没几个观众,一场下来只募了324块”,孙莉莉唏嘘道。
室外那么热,太阳晒下来,孩子们衣服湿透了,从头到尾却始终认真演出着。“我们家长,第一次看到孩子们和谐地把一首曲子完整地演出来,非常感动。”事实证明,他们也能协作,打破人们对孤独症人群的刻板认知。每次演出,家长们也挺紧张,眼睛一刻不离孩子,怕他们出差错。贝贝第一次演出,弹到中间就卡壳了。孙莉莉在一旁鼓励他“贝贝没关系,弹下去好了”。观众也给他鼓掌加油。贝贝停了一两分钟后,完整地弹完了。小岱13岁加入乐团,负责吹管类乐器,有时候表演太开心,气息也容易打乱。通过长时间的训练,表演中途哪怕忍不住笑了,他还是能够立刻又严肃起来。如今,孩子们久经沙场,很有经验,哪怕弹乱掉,很快又能接上。有次演出,电全部断掉,现场漆黑一片。家长们急得不行,孩子们却十分坦然,琴谱都看不清,摸着乐器,愣是顺溜地演奏完了。音乐让孩子们找到了自信和快乐,也让妈妈们找到了希望和方向——孩子们或许可以靠着演出获得募捐,解决部分生计;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实现他们与社会的融合。2020年5月,受疫情影响,爱特乐团线下演出全部停止,乐团一度陷入困境中。“新教室的费用还要继续交,家底快耗光了。”几个妈妈开完会,一致决定开设抖音账号。
在一家MCN机构工作的梁广添,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乐团的。他被邀请担任乐团顾问,每个月拿2000元补助,运营“深圳爱特乐团”抖音账号。
2020年7月,爱特乐团注册了抖音账号,他们在上面分享日常排练和表演的视频。2021年底,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线,他们主动联系到乐团,并协助其开通了线上募款。乐团一位家长说,“有经费后,大家心定了。”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从此,爱特乐团成为抖音站内一个特别的创作者,字节跳动公益也以此为窗口,推动公众关注孤独症孩子的就学和社会融合问题,并致力于推动和改善公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孤独症儿童就学融合之难跟整个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偏见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对孤独症群体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认为他们有智力障碍,把孤独症跟抑郁症混淆,认为发病原因是父母对孩子缺乏关爱,孩子有一些鲁莽行为是因为父母没有教好。“孤独症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先天性发育障碍,跟父母完全没有关系”,姜正红说,“孤独症有三个核心特征,社会交往障碍、沟通交流障碍和重复局限障碍,核心是社会交往障碍,即便非常少数的孤独症儿童智商很高,记忆力超群,观察力很强,也不代表他会很好地和你交往” 。公众要理解孤独症人群,这是能支持他们的第一步,理解了才能做到不歧视,接纳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有自己的权利,有上学的自由。相关人士指出,首先要对孤独症“去污名化”,不把它当成一种病,不把孤独症群体称为“患者”,而是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其次,要“去天才化”,“孤独症群体不需要被美化成天才,这一群体中天才的占比并不高,他们会演奏优美的音乐,只是因为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2023年4月2日,世界关爱孤独症日,当晚的「拾」光音乐会上,小岱、贝贝和其他乐队成员都站上了舞台的中心,表演了多首乐曲。其中,《我的中国心》难度很大,这首曲子没有固定的节奏,全靠孩子们自己控制。孩子们排练了两个多月,最后在音乐会上默契地完成了。
音乐会在抖音上进行了直播,吸引了超过1000万人观看,留下超过3万条暖心鼓励。很多孤独症孩子的父母也在活动评论区留言,表达自己的孩子收获了很多力量,希望也能学有所获,未来不成为社会的负担,被更多人理解和友善对待。在这场音乐会的筹备和直播过程中,抖音平台的很多创作者都参与进来,有音乐主播专门给孤独症的孩子们改编创作了一首《Lemon》,“讨厌着黑暗,独自行走,可却忘却了呼救”,表达对孤独症群体的理解和关爱;还有很多主播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展示才艺,弹琴、吹笛子、跳舞,呼吁社会用户关注孤独症青少年在就学环境中面临的困境,助力筹款;一些抖音创作者也加入进来,到深圳去探访了爱特乐队成员,拍摄视频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还有美妆达人去给一位乐队成员妈妈化妆,她已经很久没有精力打扮自己了。“你好星星的孩子”这个活动已经在抖音持续做了三年时间。字节跳动公益平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希望帮助公益机构在抖音等平台上更好地运营,通过短视频、直播等丰富的场景,让更多用户身临其境地看见和参与真实的公益,做好公益科普和公众价值的倡导;另外,通过平台的力量为公益机构筹集善款,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他认为,抖音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公益参与和倡导平台,它潜在能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字节跳动公益平台上有30多个孤独症相关公益项目,超过43万爱心人士为他们提供了帮助,累计爱心善款超过558万元;成立于2019年的字节跳动跳跳糖员工公益组织也已关注支持孤独症群体多年。直播的时候,小岱妈妈站在台下观众席第一排,对着台上的小岱。哪个地方没吹好,她就小声提醒他“没关系”,让他不会起心理波动。母子二人多年培养出默契,“看我嘴型、表情和手势,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最后一两个曲目,小岱完全不理会台下的妈妈,脸上一直带着笑,一只脚自由地跟着音乐打着节拍。小岱妈妈发现,在一个被排斥、被取笑、被欺负的环境,小岱肯定胆怯萎缩,而在乐团这个环境中,被保护和包容,他很轻松。“跟过去比,他的内心已经不一样。他的拘束不再是内心的问题,而是身体障碍所限。”台下的观众跟随节拍鼓着掌,孤独症孩子们得到鼓励,还以更灿烂的笑容。看着台上台下的这些人,梁广添动容地说,“字节跳动公益加入进来后,孩子们站上了更高的舞台。星星的孩子是那么遥远,我们和他们没办法在同一个世界里,但这一刻,我们是相通的。看着台上的孩子们,小岱妈妈想起他们在抖音上的第一场直播,那是2020年下半年的一天,孩子们从早到晚排练了一整天,晚上正式直播。旧教室很小,窗户对着过道,孩子们都满头大汗,有观众留言“给孩子们开一下空调,看把娃热的”。音乐会出乎意料地好,直播间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家觉得新鲜吧,没见过成年的孤独症人士。18岁以后,孩子们长得人高马大,很多被圈养在家里、特教机构里。我们乐团的孩子,是少见的敢于露正脸的团体。”接下来,爱特乐团计划在全国巡演,与更多孤独症家长互动,“用微弱的一点点光,温暖这些家庭,给他们带去一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