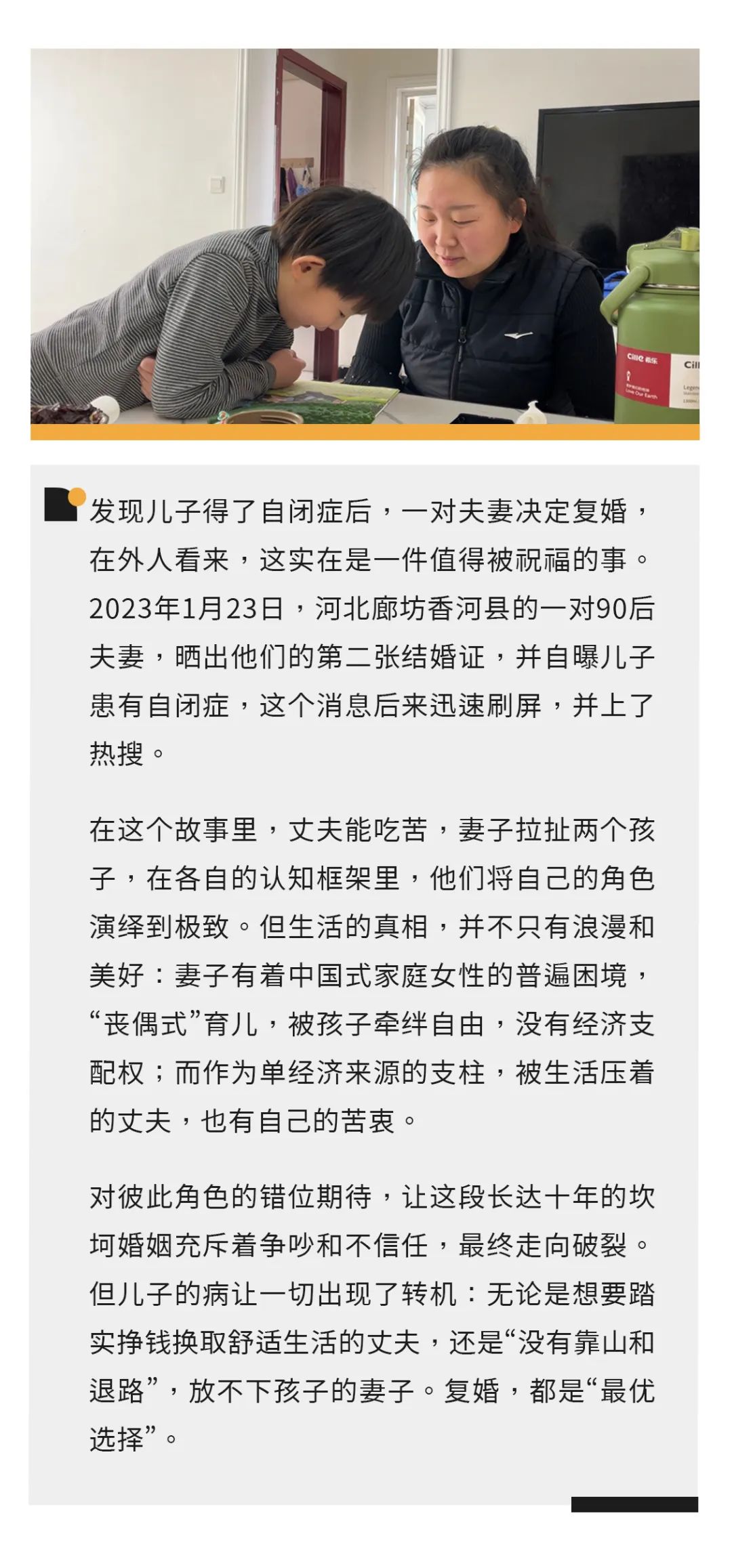
文 | 蔡家欣 刘易佳
摄影 | 蔡家欣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牢
将近90平的屋子,找不到沙发和茶几的踪影,一台空调孤零零地立在客厅,电视机被挪到不起眼的角落,进门的那张餐桌,是这个家唯一能围坐下来的地方。在崇尚家庭生活的北方县城,这样空荡的家,多少显得有些清冷突兀。
这是女主人为儿子刻意打造的空间:她把沙发从13楼拖到地下室,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都刷白了。那个木质的电视斗柜实在太笨重了,她找来电锯,果断地截掉一段桌板和3个抽屉——那是她第一次握电锯,震得她手可疼了,担心孩子捣乱,她就牺牲晚上的睡眠时间。她个子不高,眉眼很细,背有些微驼,一头长发潦草地束在脑后,额前几缕碎发不经意地跑出来,看起来疲惫极了。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位32岁女性的全部生活。她叫黄静波,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十年婚姻,她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拉扯着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上三年级,5岁的儿子倪好,在2020年7月确诊自闭症。每天早上7点,她得从香河出发,载着儿子到北京上康复训练课。将近60公里的路,儿子在车上坐不住总哭闹,黄静波只能一手扶方向盘,一手抱孩子。在厨房做饭,她得探着耳朵,仔细听儿子的动静,隔几分钟出去瞅一眼。有一回,儿子直接在防盗窗上走,她吓得腿都软了,但还得保持镇定,不动声色地将儿子抱下来。一出家门,她牢牢地跟在儿子后面,“我真的害怕,他会突然出现奇怪的举动。”她的家就在香河县城,这里到处是大型的家具城,小区门口,迎来送往的大货车轰隆隆地驶过,这时,儿子会突然朝汽车奔去。不仅如此,在游乐场,他会因为冰棍掉到沙子里没完没了地哭闹;在商场要是没给他买玩具,就直接在地上打滚喊叫。
这个小男孩个子高,长得也白净。被哭声吸引过来的人,总是不自觉地将眼神投向孩子身边的黄静波,黄静波觉得那都是指责,“孩子这么没教养,是不是大人没教好?”她觉得自己真是“太低人一等了”。但是,黄静波从来没想过把儿子关在家里。她带儿子去欢乐谷、滑雪场、海洋世界,即使从出门那一刻起,她就上满发条,攥儿子的手,总是汗涔涔的,几乎没松开过。这些年下来,她的脸皮也就“变厚了”,她说,“有段时间,我特别希望给我儿子贴上三个字‘自闭症’,这样我就能少解释一点。”康复训练课持续了两年,黄静波坚持每天往返北京香河。那时,她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母亲。她相信,儿子一定能上普通小学,“就算慢一点也没有事”。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儿子突然失去语言和互动能力,哭,是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而且一哭就是俩小时。黄静波每天祈祷,“千万别哭,不哭做什么都成。”再后来,黄静波也跟着哭,从早上起床就啪啪掉泪,刷碗哭,走路也在哭,“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这两年,她没工作没朋友,儿子就像一扇怎么都敲不开的门,她甚至想跟孩子一起走,连方式都想好了,带儿子出车祸,“还能给女儿留点赔偿款。”至于丈夫倪金磊,他们早在2019年10月领了离婚证。虽然因为疫情“离婚不离家”,但早期面对孩子的病,倪金磊更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怒吼。有一回,黄静波带着小孩在浴室洗澡,儿子和女儿都在哭,黄静波哄不过来,倪金磊终于现身了——他站在浴室门口,恶狠狠地朝母子三人吼道,“你们都一起去死!”
外人
最初,两人的故事看上去也幸福而浪漫。2013年夏天,黄静波和倪金磊举办婚礼,他们是同学也是初恋。对于婚姻,他们似乎也达成传统的一致意见:男主外,女主内。
结婚后,黄静波对丈夫的了解更深了。丈夫18岁就帮父母卖鱼,不能像同龄人那样逛商场看电影,“完全不具备享受生活的能力。”公婆控制欲强,丈夫摆摊累了想休息也不行,就连买辆货车,也得他们挑款式。黄静波心疼丈夫,把家事全揽了过来。但婚姻的裂缝悄无声息地蔓延:丈夫每天天没亮就出门卖鱼,回家就打游戏。他们几乎没有交流,除了吵架——丈夫会说最恶毒的话,“你结婚一分钱都没拿我们家来”,怀孕就嫌弃她,“你怎么这么胖这么丑?”女儿出生那天,丈夫在手术室外嚎啕大哭,朝电话那头喊,“是个丫头片子!”躺在病床上,黄静波的心都凉了。有一件小事,黄静波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婚后不久,她做好晚饭,丈夫却在电话里说,我爸今天炖猪头肉,让我过去吃。“他甚至没想过说,媳妇你也过来一起吃。”黄静波说,那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家庭的“外人”。只有在生育这件事上,自己好像才显得有价值——大女儿出生以后,公婆开始催生二胎,甚至直接在饭桌上摔筷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这样告诉自己。12岁,她的父亲抑郁症去世,之后母亲再嫁,她漂泊惯了,也独立惯了,灯泡自己换,下水道自己通。她不断反思内省,作为一个妻子,我会不会太强势了?是不是要在外人面前夸我老公?她摸索着改变,似乎改变就能换来被珍惜。丈夫倪金磊和婆婆在菜市场摆摊卖鱼,他是独子,也是家里的挣钱主力。鱼摊赚的钱归婆婆管。婆婆每月给五千块工资,黄静波生了男孩后,又加了一千块。黄静波要买奶粉,给孩子读幼儿园,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黄静波的家,为了让孩子有活动空间,移走了沙发和茶几,几乎以纯白色为主黄静波是一个对生活有想法的人。高中辍学后,她在北京做销售,每个月有万把块收入,她会到处旅游长见识。她也算爱捯饬,商家送的塑料花,她会找个花瓶装起来,再缠绕一圈缎带。她过多了苦日子,不希望女儿有匮乏感,自己牙齿坏了,200块钱也舍不得花,同样的钱,她每年都给女儿拍一组写真。
但在婆家人眼里,这些是不本分的信号。没攒下钱,就被指责不持家,有时甚至连买一个置物架,也会被吐槽。过了十年日子,在钱的问题上,黄静波从没被信任过。有一回过年,她带着孩子在公婆家吃饭,丈夫突然开口,“吃完你带孩子先回去吧。”黄静波明白了,他们要开始算一年的总帐了,而她不能在场。在这样的挤压下,黄静波明白了婚姻里的残酷现实:把家照顾得再好,没挣钱就没有优点,都要看别人脸色。“我要是一个月能挣1万,他们肯定什么都不说我。”2018年5月,儿子只有9个月大,黄静波在县城开了一家童装店。她前后花了20来万,这笔钱来之不易,有她压箱底的彩礼钱,倒卖家里二手车的钱,找母亲借的钱,以及丈夫和婆婆给的六万块钱——在她的游说下,丈夫和婆婆抱着“经济也能支撑,可以试试”的心态。即便如此,家里的争吵还是越来越频繁。黄静波揣度过,他们也许心疼本钱了,也许是埋怨她无法平衡家和生意。她很疲惫,感受不到一丁点儿被理解。2019年10月,黄静波提出了离婚,房子车子全在倪金磊父母的名下,她净身出户。赶上了疫情,只能“离婚不离家”,她和倪金磊约定,自己带女儿,他管儿子。
错位
位于香河县城的三强农贸市场,紧挨着香秀排水渠,灰扑扑的市场,路歪七扭八,摊位都拼命往路中挤,行人电动车一多起来,腐烂果蔬混合蒸屉里的包子香气,腥味越来越近,菜市场东南角是个大鱼摊,老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理着光头,穿高筒水靴,围兜盖不住他那滚圆的肚子,上面溅满了鱼的血水和鳞片。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凶,却是一把干活好手,他用单条大花臂从水里捞出一条活鱼,狠狠摔在砧板上,然后拿木棍敲鱼脑袋,再用除鳞机在鱼身上滚几圈,最后抄起剪刀挑出鱼内脏——不到半分钟,一条鱼就“呲”好了。那就是黄静波的丈夫,32岁的倪金磊。这个20来平米的摊位每天进出两千多斤鱼,至少一半得靠倪金磊一条一条“呲”。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得爬起来,一直站到中午11点收摊,下午3点再回市场备货。隔几天,他会去20公里外的鱼塘收购钓的鱼。市面上鱼的批发价4块8,“我3块5弄来,4块钱给他们,我挣5毛,他们省8毛。”他精明而务实,为了多挣这点钱,收鱼的晚上10点出发,最早也得凌晨1点钟回家。做这行十年,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和疫情,倪金磊几乎没有休息,即便感染了奥密克戎,他也只在家躺了一个下午。在这个河北小县城里,每个月能挣两万块,家里有三套房两辆车,几乎“顺风顺水,要什么有什么”。倪金磊唯一称得上爱好的是“耍手机”:刚结婚时,他往游戏里充值大几万;现在是看剧看小说,烽火戏诸侯的书,还有《天龙八部》的电视剧。在朋友程文彬的眼里,倪金磊是个好男人,只抽烟不喝酒。一群朋友中,就倪金磊活得不像90后,“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像他这样吃苦。”不仅如此,倪金磊还很有勇气。就在要跟别人订婚的前一天,倪金磊重新遇到初恋黄静波。他想退婚,很多朋友不赞成。最终倪金磊听从了内心。这些往事,倪金磊只有轻飘飘的一句话,“见色起意,也知道她原生家庭不太好,挺想保护她的。”婚后的生活却一塌糊涂。在倪金磊的世界里,夫妻有各自的功能角色:“丈夫是耙子,妻子是匣子,一个划拉钱,一个管好钱。”他觉得自己还算一个合格的丈夫,“没缺你吃,没缺你喝,要钱给钱就行。”他承认妻子顾家。至于管钱,他摇了摇头。她朴素,大钱也不花,但三五百的小钱,“碎着花都花傻了。”闺女学滑板,一连买了好几个板;小孩骑的车,家里也有好几辆。闺女英语、奥数、硬笔书法换着来,最近又报了古筝课。倪金磊没同意,妻子直接找婆婆要钱,又花了大几千。说得多,他也担心闺女误会,“整得咱不舍得给她花钱似的。”
中间有一年,由夫妻俩管钱,再给婆婆发工资。那一年,家里添置了小货车,没攒下什么钱,倪金磊只能归还经济权给父母,反正“他们又不会瞎花,也不会给别人”。妻子的很多行为他不理解,“女人需要的太多了,得能挣钱,还得陪伴。”结婚头几年,妻子总要扳正他玩手机的习惯,好多次回家,她又拉着脸,“我在外面挣钱,回来还要哄着你,那谁来哄我?”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回来就想一个人待着,清静一会。”他的婚姻字典里,没有陪伴和交流的概念。妻子产检、孩子生病,或者捯饬家里,他就一个理:“你爱去就去,爱做就做,我不拦你,但也别想我陪着。”妻子跟他讲道理,他就跑房里;给他发信息,他看都没看,全都删了。对他而言,钱是生活的要义。“我哪知道啥叫幸福?反正钱够花才叫过好了。”倪金磊经常感到遗憾,“结婚早了”,后悔该“多自由两年”。婚后不久,妻子就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都跑产检住娘家。大女儿出生后,三个人陡然凑一块,他还觉得“别扭”,“不自在”。不过,离婚的念头他没动过。妻子提离婚那天,两个人起了口角。妻子的真实想法他不知道,但隐约觉得“她离不开孩子”。恐惧也是真实的,他害怕妻子对这个家撒手不管,“我连钱都挣不踏实了。”钱,钱,钱。只要不碍着挣钱,他就不把事往心里装,“在我眼里,除了人死是事,挣钱是事,其它就都不是事。”他哭着挽回妻子:“媳妇,这么多年,你对我太包容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生气。”但妻子态度坚决,他也自知理亏,最终两人还是领了离婚证。
双面胶
离婚后的生活反而“顺”了:黄静波的生意有了起色,最好的月份销售额达七、八万。大年初二,倪金磊主动提出到北京看望丈母娘。之后疫情居家,黄静波做饭倪金磊洗碗。不仅如此,倪金磊还会拉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转圈。黄静波说,“这是她第一次有家庭的感觉。”一切都因为儿子的自闭症而告终。2020年7月份,黄静波的儿子确诊自闭症。“我以为要结束那种生活,又掉进另一个深渊。”黄静波说。她关掉童装店,疫情生意受影响,投进去的本几乎没回来。儿子看病又没存款,她陷进更深的自责里。许多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她不断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开童装店,儿子的病是否有一丝转机?“要是我能早一点发现呢?”沟通的问题,经济权的问题,现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她和丈夫达成了共识,就是给孩子看病。最初,他们手上没钱,倪金磊又不敢跟父母开口,怕他们埋怨黄静波。最后,倪金磊,只能卖了自己6万块的金链子,加上妻子1万的首饰钱,暂时渡过难关。儿子刚确诊时,倪金磊也想不通,在车里流着泪给姐姐打电话 “别人家孩子都正常,怎么摊上我这就不行?”他干啥都觉得没劲了,“挣半天钱,回头儿子连花都不会花。”愤怒、郁结的情绪都撒给家里,那段时间,夫妻俩最长曾七八天没讲过话。前年开始,倪金磊慢慢接受现实。他又找到挣钱的意义,“多给儿子留点钱,包办他下半辈子”。至于闺女,他也想多给点陪嫁,“让她不用(因为弟弟)受委屈”,“甭管是谁,谁有钱谁硬气。”这两年,他也发现了黄静波对这个家的重要。除了她,“没人能看得住这个孩子”。儿子生病,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个转机。黄静波说,当时提离婚,只是想吓唬一下他,没想到丈夫真同意了,自己反倒“被动”了。直到儿子生病,黄静波又多了一个不能被取代的功能,成为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唯一人选。婆婆开始主动给黄静波发红包,让她给自己买点吃的。在外头也跟人夸,“这几年真苦了小黄。”私下还劝倪金磊,“小黄不容易,你回去不要跟她干架。”倪金磊也理解黄静波的苦,“起码我在外边卖东西,想跟谁聊就聊”,但妻子只能跟孩子绑一起,“她真的比我厉害,比我坚强,说真的我扛不住。”这个家似乎又达成了某种平衡,夫妻俩终于能平和地坐下来聊天。大部分时候,黄静波讲孩子的上课和闯祸,倪金磊听了,一句“能咋办?”终结话题。女儿五子棋比赛得了第一名,黄静波现场打电话报喜,倪金磊听完,“嗯啊”就挂了。偶尔倪金磊也会主动开启话题。在抖音上刷到房车旅行的视频,他和黄静波聊起未来,等攒够钱,就买一辆房车,带儿子到处玩。这是他最羡慕的人生了,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只出去旅游过两次。作为父亲,倪金磊也开始分担家里的情绪:儿子闹腾时,黄静波一个人跑房间哭,倪金磊主动放下手机,先哄儿子,转过头再去安慰黄静波,“咱们尽力治疗,多给他留点钱。”2022年疫情,黄静波和两个孩子不敢出门,倪金磊半夜出摊,早上顺道买菜回来。尽管他对钱还是不大方,脾气来了,对孩子老婆视若无睹,但黄静波发烧了,他就悄摸摸把饭煮了。黄静波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去年年底,黄静波向倪金磊坦白信用卡欠了10来万。这些年,倪金磊虽有给钱,但并不爽快,多则两万,少则两千,碰上疫情孩子没去上课,他也会缩减生活费。这些钱覆盖不了家庭所有开支。而且为了儿子康复,黄静波私下也各种砸钱上课,最后只能套信用卡。实在兜不住,她只能坦白。倪金磊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借钱,“媳妇贷款还不上,我这有点急,你先转点过来。”黄静波有点动容,“没想到他会帮助我,他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难念的经
她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只有复婚了才是真正的夫妻。”这或许也是她当下最好的选择,“有房有车,老公能挣钱,爷爷奶奶还有点家底。”更大的担忧是,如果她真的离开这个家,不仅又要过回漂泊的生活,而且“儿子肯定没人管。”起初,倪金磊并不同意,“你想离就离,你让我复婚,我就得跟你去?”黄静波听到这话,“心里头几乎都乐了”。她对丈夫的“狠话”太了解了——倪金磊在表示“需要被哄”。黄静波没什么可犹豫,直接哀求他:“老公,我真的爱你需要你,一家人都离不开你。”今年1月23日,这对夫妻终于复婚了。黄静波把视频放到网络上,视频下全是祝福的声音,“患难见真情”、“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最近这些天,黄静波忙着回应记者。家里变得突然喧闹,9岁的大女儿倪梦琪,几乎都是安静地坐在阳台的书桌上,写作业上网课。父母离婚的事,她是从母亲的小红书上看到的。离婚意味着什么?这个9岁的女孩想了很久,小声说,“相当于我没有家了。”但是,在她的印象里,家好像又没变化。她的镜片特别厚,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思考了。她说,离婚是因为我小弟。在她眼里,妈妈简直为小弟操碎了心。小弟闹脾气,妈妈就会躲起来哭。这时倪梦琪会凑到妈妈身边说,“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不结婚不找男朋友,我挣钱养他。”小弟确诊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把人生的希望抛给了她,每天给她发卷子,盯着她写卷子。这个小女孩不介意,她甚至希望自己更懂事,“这样妈妈可以轻松一点。”关于这个小弟,她也困惑过,“为什么别人的弟弟挺聪明的,我的小弟有点傻,容易被人笑话?”每回出门,这个小弟总要制造点麻烦——现在她都习惯了,带着稚气的老成,“不用劝他,他自己哭着哭着,哭过那个劲就行了。”不过,这个9岁的孩子最大愿望还是“能跟妈妈单独出门玩”。复婚后的生活照旧:每个夜晚,倪金磊在餐桌边玩手机,黄静波就陪儿子读绘本,女儿自己写作业。偶尔,儿子情绪不对付,发脾气喊叫。倪金磊安慰自己“人是傻点,颜值挺高”。黄静波想的是“一人一个活法,儿子选择比较轻松的”。某种程度,作为妻子的黄静波还在妥协。到点了,她自觉领着两个孩子睡南卧,倪金磊自己睡北卧。和丈夫发微信也点到为止,想再探讨一句都犯难。倪金磊坦言,如果没有儿子,对离婚无所谓,现实是“儿子离不开妈妈,他妈妈还得负责。”黄静波也知道,是儿子捆绑了这段婚姻。她无法也不愿意离开,打算就这么熬着,起码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阶段,现在相互扶持”。钱,依然是敏感地带。倪金磊给过黄静波6.2万还债。黄静波跟他对过两年的帐,他看起来不太相信,年后,再没给过一分生活费。黄静波有点伤心,但也透彻,“(我)把经济大权拿过来就行。”只有在某些时刻,“夫妻共患难”的真实感才会浮现上来:在菜市场,倪金磊曾见过一对老夫妻领着一个男孩,十七八岁,高兴起来“嗷嗷”地叫,还到处跑,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家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