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花落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名字传来,大家一片茫然,这究竟是谁?

瑞典文学院给予她的颁奖词是:
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与集体限制。

其实别说咱们不知道,安妮的知名度不算太高,她成名早,一度文学圈还瞧不起她,觉得她的东西过时,被人轻薄地视为“那个写自己的女人”。
安妮·埃尔诺也已经82岁,早过了想要争名夺利的年纪,这么些年,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当老师,写作攒下的身家,静静地隐居在巴黎郊区的塞尔吉,与外界没什么联系,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瑞典文学院想尽办法也还没能联系上她。
一直到消息宣布,82岁的安妮在位于巴黎郊外的家门口才被闻讯而来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她也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



此前,法国已经有15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埃尔诺是第16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但之前的15位都是男作家,她是第一位女作家。
她也是继2020年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之后,再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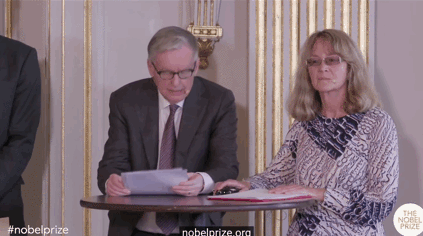

▲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现场。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埃尔诺表示,获得诺奖促使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责任感。

跟绝大多数把目光投向大时代,投向世界的男作家不同,埃尔诺作品的体裁很“专一”:自传体作品或者类似的回忆录。
其实内地也有专写这种体裁的女作家,十来年前内地文坛也有所谓的“身体写作”“私写作”潮流,埃尔诺1974年的处女作《空壁橱》就是写自己私生活,时间之早,可谓“私写作”的奠基人。
无论后人如何模仿,但都达不到她的高度,为什么?因为虽然都是自己的生活,但大部分人写的是个人的自传,而埃尔诺则是借自己的生活去见证法国的大时代,她的个人史家族史完整地跟法国战后的生活史紧紧相联,她如何从底层女性变身成为富裕中产少妇,父母的杂货店如何因为法国经济生活而起伏,母亲那代女工会省吃俭用买《时尚》杂志、人们用一种叫做“玛丽花”的疥疮药……
跟埃尔诺合作过31年、将她的作品出版成英文版的出版商丹·西蒙曾如此评价:
她写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字,都是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真实。然而,这些同样也是想象力的杰作。怎么样?这句话似乎听懂了,似乎又有点听不懂吧,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位年过八旬仍然智慧矍铄的女作家的人生故事,她从一个杂货店体弱多病的穷女孩到82岁才名扬世界,34岁发表处女作,43岁成名,60岁退休才开始全职写作,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位女性写作者要经历如何的艰辛才能成就自己。安妮·埃尔诺她这一生究竟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才能打动万千人的心呢……
安妮·埃尔诺这一生经历过什么,根本不用采访,因为几乎都在她的小说里了。1940年安妮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父母在当地经营杂货店和咖啡馆,在她之前,她还有一个姐姐,七岁时夭折了,所以她是父母的宠儿。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在埃尔诺眼中,他们有时是个好父亲、好母亲,有时却变成坏父亲、坏母亲。安妮的父亲,年轻时是个英俊而靠谱的男人,“高个子,褐色关发,蓝眼睛,看上去特别挺拔俊美,至少父亲自己这么认为”。他一辈子都很向上,可以说他是把安妮从低层生活里托举出来的第一步,祖父酗酒暴力,不喜欢有人当着他的面看书,父亲十二岁就不得不出来工作,先在农场,后来又去工厂做工。“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就是说,做一个一个工作,既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乱花钱,他喜欢看看电影、跳跳查尔斯顿舞,但从不去酒馆……他是工厂里第一个为自己买了辆自行车的人,每周他都有存款。母亲可能就是因为看中父亲这方向才爱上他的。”

▲ 埃尔诺父亲。

后来父亲遇到了母亲,母亲比父亲小7岁,两个人都是不甘平凡与贫困的人,婚后两人苦挣苦捻才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尤其在冬天 ,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从来不开灯,他们俩摸着黑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母亲站在炉火旁边忙着什么,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了。
“这个咖啡杂货店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在塞纳河下的工作上找份活干,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干活,”
母亲必须一边看孩子一边微笑着做穷苦人的生意。
▲ 在这张和父亲的合影中,埃尔诺的父亲之所以眉头紧锁,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是因为担心拍照的妻子会把相机弄坏。埃尔诺曾在书中回忆道:12岁时的某一个周日的下午,她亲眼看到父亲差点杀死自己的母亲。在打打闹闹中,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终于得到一些改善,渐渐脱离了贫困线。
▲ 这是它如今的样子,安妮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是父亲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对母亲来说,这实现了她多年来想在楼上有房间的梦想,一个餐厅,一个有穿衣镜和大衣柜的卧室。▲ 曾有记者走进探访这座有园子的老房子,曾是一家人的骄傲。父亲一辈子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他要求自己和家人都说标准法语,在家庭餐桌上练习巴黎人的礼仪,要求女儿“有教养”并考学,他自己则骑着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无论冬夏,风雨无阻,他对于女儿拿到奖学金读大学十分的满意,对于女儿带回来的朋友有着份外的热情,因为他生存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进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女儿成功了,她考上好大学,而且还嫁给了出身高知家庭的丈夫,为了迎接这个来自较上层社会的准女婿,埃尔诺的父亲特意换了新衣服,还打了领带,带着他逛自己的菜园、修建的车库,希望能在准女婿面前赢得尊重与承认。但婚后,埃尔诺常常一个人带着孩子独自回娘家,丈夫并不陪同,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态度。父亲对于这样的生活很满意,他收拾房子,看顾小店,因为胃病,死于1967年。母亲出生也很苦,很小就失去父亲,出生在一个孩子很多的普通家庭里,她“是个谨慎的女孩,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去做弥撒,自己熨床单,绣嫁妆。”她洁身自好,喜欢看书,她用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不晚上出门,生怕没有“好小伙子”娶她。后来,她嫁给了埃尔诺的父亲,一个比她大7岁、相貌堂堂的工人小伙。

在女儿埃尔诺眼里,母亲的形象风风火火、前一秒对你破口大骂,下一秒又抱着你叫乖乖。有时,她也会陪着女儿谈文学、读诗歌,和父亲一样,在女儿结婚时,她也千叮咛万嘱咐,让女儿和女婿好好过日子,“别被人家休了”。母亲一直勤勉,哪怕晚年被接到女儿女婿家,也要非常勤力地带孩子,生怕别人嫌弃她,一直为女儿嫁到这样的好人家而感到自豪。▲ 中年时的埃尔诺和母亲。1983年,埃尔诺和丈夫分居,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后来又把母亲接来一起住,但在晚年,她的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记忆错乱、脾气暴躁乱骂人甚至动粗等等,曾让她苦不堪言,最后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并在那里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