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之变”。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性,它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哪些问题,中国大陆的‘性’经验在今日能够带来哪些边缘叙述和跨界对话。这项工作和我以前那些具体的、细碎的研究不同,我希望能够将林林总总的现象和研究汇总起来做一个比较宽泛的整体性思考。

我对性问题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生时代就开始跟着潘绥铭老师一条道走到黑,另一方面是因为性的两重边缘性让我很感兴趣。
“性”具备一种日常而边缘的特点,说它日常,是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经验它、谈论它,媒体也在报道它,法律和治理活动也在关注它,但有关性议题的研究在学界又极度缺乏。我曾说性议题是学界的弃婴和媒体的宠儿也不完全是开玩笑。此外,性议题带着很强的道德色彩,跟政治紧密联系,很多政治斗争都在使用涉黄、生活作风等语汇,一定要把二奶、三奶扒出来。性和经济的关系也很密切,比如和同志文化相关的粉色经济、性玩具产业等等。我们看到,性是一个和道德、政治、社会规范、商业、媒体、医学等领域都有关联的议题。
潘绥铭 / 黄盈盈,《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性在东西方构建有关对方的想象时也很关键,这种想象甚至会影响到老百姓的认知。比如有一段时期我们谈论性问题时经常说一些不好的现象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来的。八十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宣传也把它和西方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至于是哪个西方,西方到底有哪些生活方式,人们是不关心的。但是在想象西方的时候,性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反过来,西方在想象东方时,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例如西方很多学者对春趣图、房中术、裹小脚、娼妓文化、男风等现象很感兴趣,把它们看作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的特征。东西方如何通过性来构建对对方的想象,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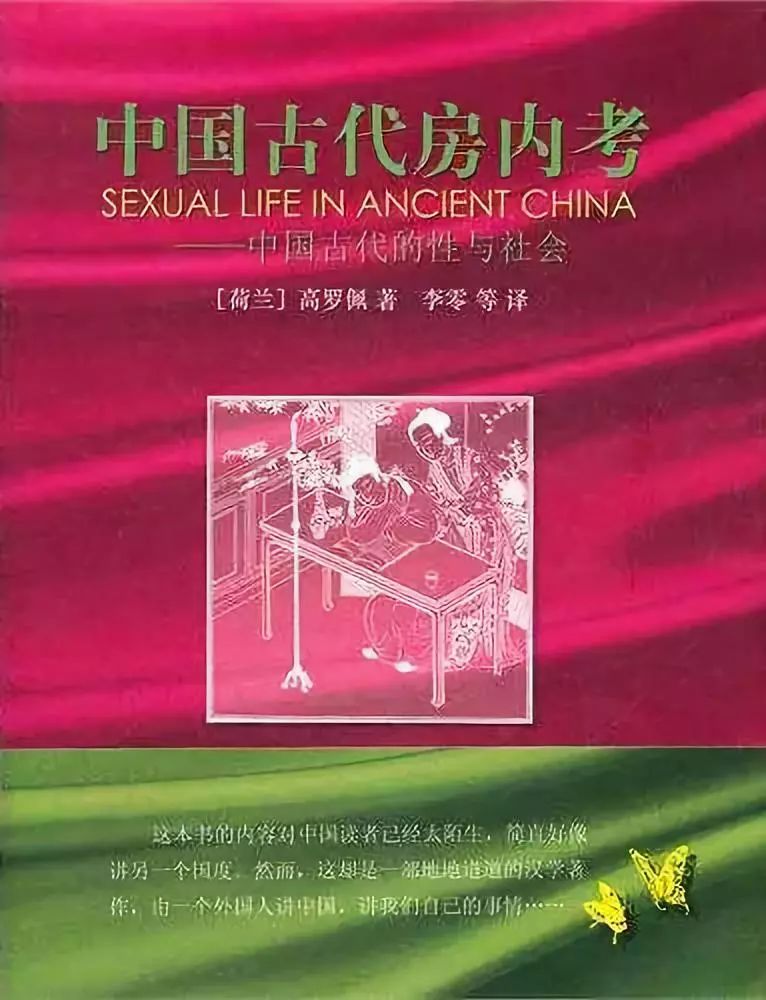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关注八十年代大陆的性变迁,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作为一个七〇后,对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境有比较多的亲身体验。我立论的基础是潘老师和我做过的一系列研究、对变迁社会的观察和已有的研究文献,还包括研讨会等半学术活动的经历。我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二是该现状发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最后是中文学术界的语境,这是我对话的主要对象。
我将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的性变迁划分为四个时间段。起点是建国以后至八十年代之前,这个时期是变迁发生的背景。潘绥铭老师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无性文化”,我的概括是“去性文化”和“高度政治化”。
生活在大陆的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时期的服装、影像和语言都是去性化的。有一件和性有关的大事,就是新中国一举扫黄成功。北京和上海动用军队关停了很多妓院,并且对扫黄运动的描述都在使用阶级话语:妓女是受剥削的阶级姐妹,而老鸨是阶级敌人。妓女经过治疗和改造,最终走上学习、就业和结婚的生活道路。

我和潘老师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经常能听到这种说法:当时扫黄能够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这种说法包含了很多信息,一是描述那个时代所使用的纯洁的、理想化的话语,一是对当代许多现象的不满。按潘老师的话说,这一时期“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无性文化,形成了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发生性行为了,而是性行为的合法性被限定在生育上面,因而六十年代也形成了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
此外,样板戏里的人物和人们的日常装扮都是去性化的。对男女流氓和坏分子的打击,也体现了性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可惜社会科学对这一时期的性仍然缺少研究。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
在上述背景下,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性变迁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包括潘老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怎么定义性革命?第一,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性文化;第二,这种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生;第三,这种变化不是只出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按潘老师的总结,性革命表现为五个层面:第一是性哲学层面,唯生殖目的论不断受到挑战,性快乐论逐渐兴起;第二是性表达,包括语言文字和身体着装的表达,至1992年10月,有关性知识的书籍已出版二百七十多种,这一时期被称为建国后的第一次性学热,人们关注身体、装扮身体的意识也开始复萌;第三是比较隐秘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层面;第四是性关系层面;第五是性与性别层面,如女性的性与身体、多元性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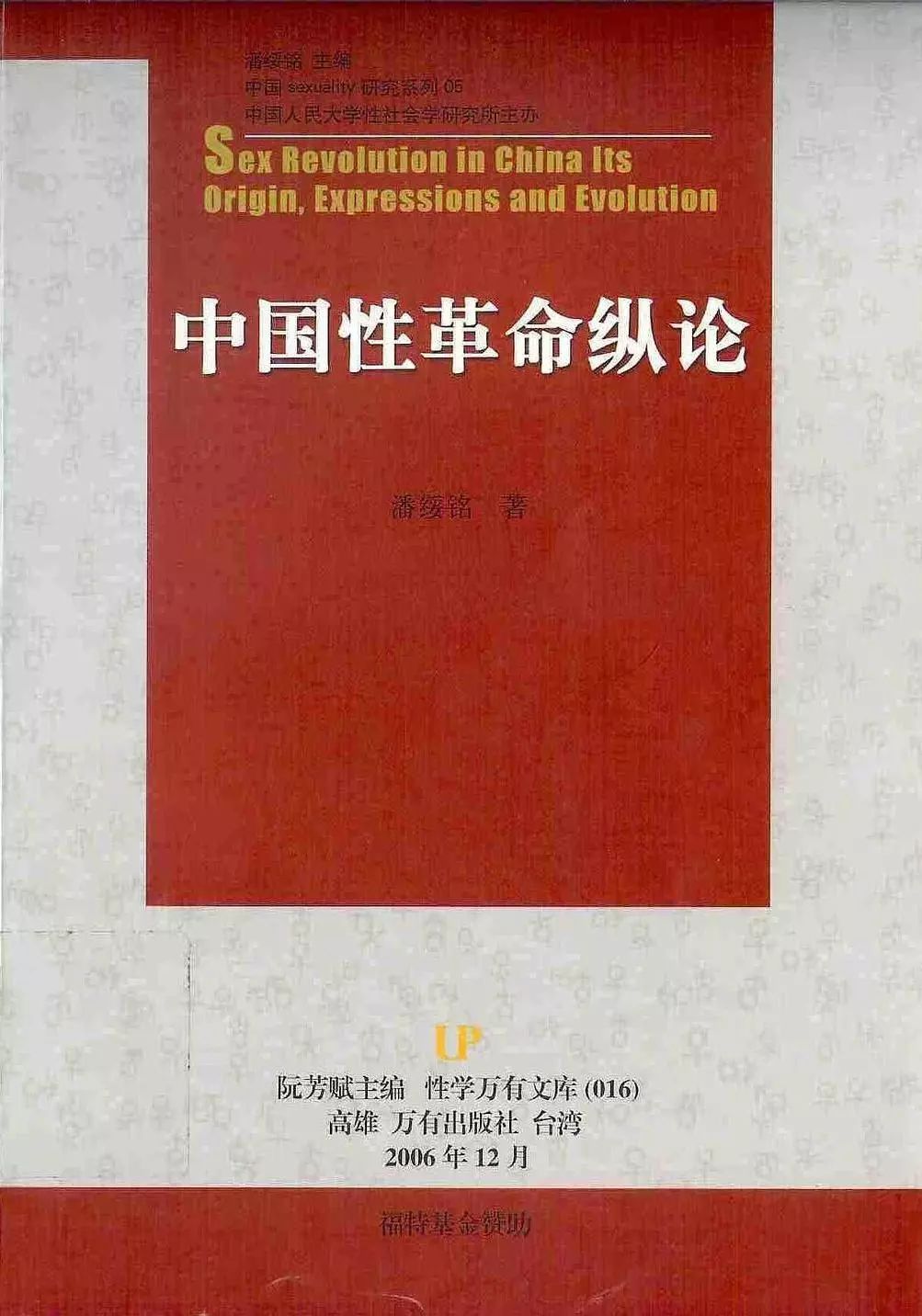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万有出版社(中国台湾高雄)2006年
我们来看八十年代的几个例子。
有个叫郎景和的医生写了一篇文章,叫《新婚性卫生》,当时的流行程度可以和今天的耽美文学媲美。1983年第一例公开报道的变性手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85年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性知识手册》和《性医学》,这两本书影响非常大,代表了性知识在科学主义和医学话语下的返潮。
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人体油画艺术展,同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性学研究中心,创办了《性教育》杂志;1990年《人之初》创刊;1994年北京举办第一次性知识展览,同年中国性学会成立,一时吸纳了上万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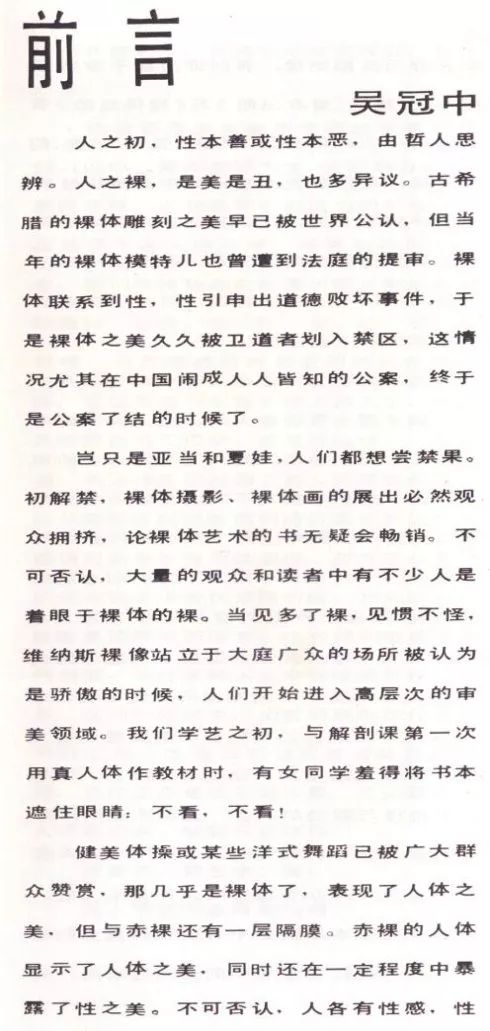
1988年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画册及吴冠中先生撰写的序言
1989年潘老师翻译了《金赛的性学报告》。很有趣的一点是,八九十年代的性学书籍都使用美女照片作为封面,而且人们多是在地摊上花几块钱买到这些书的。这段时间还创生了很多中文的性词语,比如“做爱”就是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词。1993年李银河老师和王小波合写了《他们的世界》,在同性恋人群中影响力非常大。1994年张北川老师出版了《同性爱》,但影响不如李银河大。1997年《东宫西宫》面世,不过很快就被禁了。
回过头看1983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严打。迟志强是一个当红演员,由于和若干女子在自愿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被判了四年。当时有人因为偷看女厕被判死刑,某女子因为与十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被枪毙,大家可能觉得无法相信。
八十年代男性流行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女性流行烫大波浪,迪斯科也开始兴起,这些都是革命性的身体表达。当时很多人看不惯这些现象,北京就发生过围剿喇叭裤事件,还有热心群众给《北京日报》写信呼吁“不能让这些青年堕落下去”。

把这些现象和当下做一个对比会很有意思,比如这几年上海的来来舞厅又开业了,但主要的消费人群已经变成了中老年男同性恋人群,再比如最近类似“不能让青年继续堕落”的声音又出现了,有的说少年娘则国娘,有的说大学生艾滋病传染率很高、大学生要洁身自好,不能堕落下去了。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变化趋势可以用数据说明。八十年代引起社会热议的问题主要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有关爱情的大讨论等等。但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说婚前性行为难道还算个事儿吗?不过婚外性行为还比较严重。
八十年代“陈世美”现象很受关注,1982年还出现了一个“秦香莲上访团”,就是一些丈夫出轨的太太组织起来上访,一直访到北京。1980年的《婚姻法》修改也很重要,新法规认可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离婚,很多人开始追求“爱情”,和原先的配偶离婚。很有趣的是,上访团希望借助组织的干预保卫婚姻,可是组织也管不住,离婚成了一股浪潮。相应的,傍尖儿、情人、毛片儿等词语也在日常生活中流传开来,有人把毛片儿叫做带劲儿的。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用哪些词语谈论性现象,基本上就能判断他的性观念和所属阶层。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点数据,我喜欢从很多年累积的数据里发现变化和趋势。
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做大学生调查,1999年开始做全国18到61岁人群的随机抽样调查,每隔五年调查一次。先来看全国人均的多伴侣情况,2000年到2015年的四次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们终生累积有过多个伴侣和上一年有过多个伴侣的比例都在上升,男性的终生多伴侣比例从20%增长到近60%,女性是从10%增长到30%。在已婚或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有过外遇的比例也在上升,男性的比例从12%左右上升到35%,女性是从5%上升到15%左右。
这些数据能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确实更加开放了,一是人们越来越敢于在调查中表露这些事情,这两股力量共同造成数据的上升趋势。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中国的性革命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
性、爱、婚三者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夜情挑战的不止是婚姻,还有“爱性一致”的观念。我们看数据就能发现,对感情质量和性爱质量满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而对婚姻满意的比例在下降。那么婚姻到底是什么,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婚姻对不同的人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再看大学生的性现状。有过性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一直在上升,但也没有超过30%。反过来想想,超过70%的大学生并没有过性活动。媒体经常报道大学生乱套了,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在有过性经历、已经同居、曾与多人性交三个指标上,大学生的比例远低于同龄的非大学生,百分比差两三倍。大学生比非大学生乖得多,所以大学生不能轻易被贴上高危的标签。
西方学者也关注中国的性革命,但他们是按西方性解放的脉络来讲述中国经验的。潘老师等国内学者认为并非如此。中国的性革命并非国外思潮的传播所推动的,而是有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如单位制解体、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衰弱、人口流动性的上升、居住方式变化等等。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推动性变迁的力量,对一些特殊人群意义尤其重大。对同性恋人群来说,互联网交友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两项政策的出台也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一是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一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挑战了唯生殖论、助推了快乐主义的性哲学。

八十年代整容手术(摄影:刘香成)
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初级生活圈是潘老师提出的概念,即性别、性、家庭、婚育等和我们生活最相近的领域。比如说生殖技术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婚育的模式和可能性,再如性别和跨性别问题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无法接受这些话题,但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一定要睁眼看世界,看到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眼睛一闭了事。学界有人问我小姐是非法的,你怎么能研究她们呢?我的回答是,不管小姐违法不违法、你个人喜欢不喜欢,都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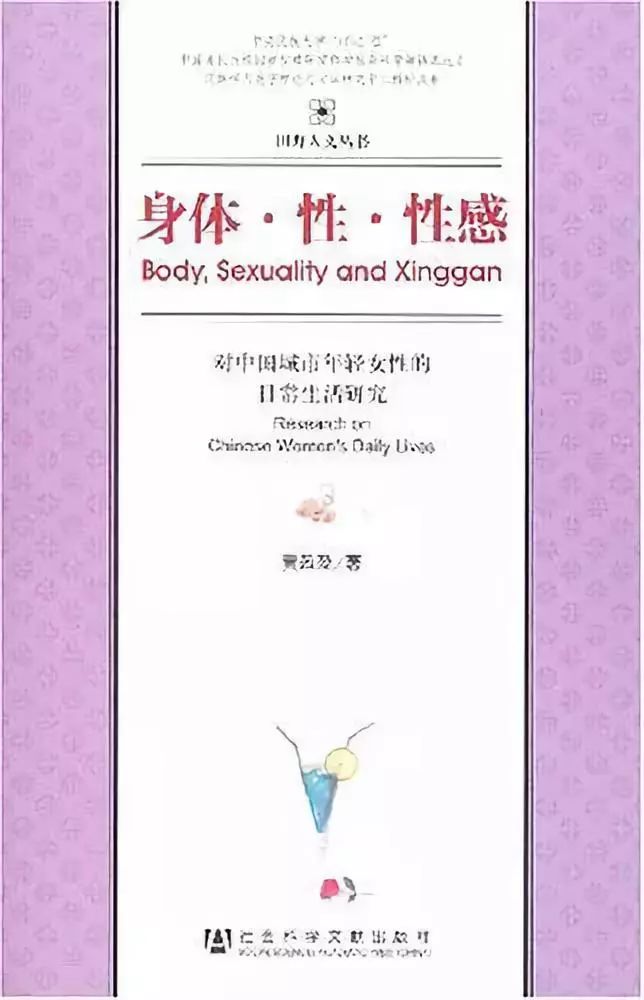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再如虚拟技术的发展会给性活动带来哪些变化,都值得观察。性别比例失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女男人口比都到1:1.22了,很多人口学学者就会简单推论说性别比例失调会造成很多光棍,光棍不是去找小姐就是搞男男关系,但实际上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光棍问题和贫困、和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而不是性别比造成光棍这么简单。就算男女比例是1:1甚至倒过来1.22:1,只要贫困人口还存在、人们对婚姻的认知不改变,还是会有很多光棍产生。

05
“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
和性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艾滋病。2000年以后很多防治艾滋病的国际项目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高危人群的标签,如卖血、静脉注射、女性性工作者、性病门诊患者、长途卡车司机等等。2005年以后MSM人群(男男性接触者)也被贴上高危标签,最近在校大学生也被贴上标签。
这些高危人群的标签或形象是怎么被疾控部门和媒体生产出来的,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安全性行为,以及与之相应的风险性行为,媒体开始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性传播在七八年前就占比很高了,但近期为何作为一种现象被重新关注?我觉得这类强调艾滋病性传播的报道会在大家心中造成一种临近感,让大家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能遇到感染风险,这背后透露出的健康治理的系统和策略非常值得琢磨。这类报道惯用的策略是数字加上故事讲述,数字会引起你的焦虑或者恐惧,故事又让你产生临近感,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很多十万加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这些策略利用的是人们心底很深的道德恐慌和情感的脆弱性。

那么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关注什么?
首先可以看到定量调查和医学话语的使用不断得到加强,其次是对安全套使用、性交频率、多性伴等问题的持续关注。此外一些特殊人群也会受到关注,如女性性工作者。其实小姐的感染率一直不高,但她们一直被当作高危人群。还有MSM人群、农民工、老年人、大学生都被轮番拿出来贴上高危人群的标签。比如那些有关农民工的报道逻辑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他们独身出来打工,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倾向于找小姐,感染以后又会流动到其他地方等等。这些报道不关注农民工的真实处境,而是给他们贴上了新的歧视标签。还有一些艾滋病防治的项目做得也不聪明,比如有的机构把小姐聚集起来培训怎么使用安全套,实际上小姐的健康知识比他们强多了,不需要他们来教。

《积极生活:HIV与我的生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下面我们再看看2010年以后风起云涌的性与多元性别。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都在发生变化。有几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2010年以后扫黄力度加剧,1981年禁止卖淫嫖娼的法规面世后,我们又扫了三十多年黄,但2010年这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上往下扫,从五星级开扫、全国范围内持续扫,而以前都是从站街女扫起,各地分头去扫。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莞式服务,结果扫黄报道一出,大家都去查东莞三十六式有哪些。禁止反而起到生产的作用,这点福柯有过洞察。我和潘老师想看看扫黄对性服务行业有什么影响,去红灯区调查过几次,我们发现大家不会因为扫黄就不做这一行了,而是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了。比如有的小姐从门面转到线上经营,有的开始只接熟客等等。
还有一个现象是整个LGBTQ群体的显化。八九十年代这些群体也有活动,但活动的形式和空间都比较隐蔽。但是2010年以后,很多倡导式的活动出现了,活动跟国际的接轨越来越紧密。还有Blued、Aloha等APP的兴起,这些应用对LBGTQ群体的影响非常巨大,对他们的交友频率、交友模式都有颠覆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现象是性议题的青少年化,青少年不再是单纯的受众,而是慢慢成为了性教育的主体。这背后有UN对身份政治的推动力量,比如我和一个小姐同时做小姐研究,UN一定会优先资助小姐,因为我属于旁观的既得利益人群,青少年的情况也差不多,UN觉得青少年的性教育由青少年自己做比较好。
与此同时,反性力量也在崛起。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安性博会上,反性大妈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大骂参与者道德败坏。以前还有研究性的学者被人泼粪的。大妈们认为从事性产业和性研究的人败坏了社会道德,尤其是教坏了孩子们。
在这些纷繁的性现象之下,我想问的是我们对性的了解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对性的讨论触碰到更多真问题了吗?我们的性话语是不是更加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对于性这样一个国际联动紧密的话题能够提出哪些本土思考?在性这一富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领域,我们如何体会和论述中国经验、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在今天的分享中可以回答的,姑且留给大家一起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