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妈妈笑着说,他们家的经济策略就是只生一个孩子。
撰文|李心怡
编辑|沈佳音
“中产阶级”曾经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你可以养育两个孩子,去高质量的公立学校。
它意味着拥有一栋房子,不需要多大,但是是自己的。
它意味着工作日六点准时下班,和家人一起欢度周末。
对于现在很多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32岁的马特·巴里是美国加州一所公立高中的历史老师。每周五天,他在学校教课,课余和周末,他又做起了优步司机——为了多赚些钱,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打好经济基础。
巴里在接单的间隙批改作业,有时他会想,如果自己没有开车,此刻应该在备课。
巴里的妻子也是教师,他俩的年薪都是6.9万美元。他们二人组成的家庭原本是中产阶级的坚实一员。
然而,科技热潮带动了硅谷当地的财富暴涨,物价和房价随之飙升,远远超出了长居于此的普通人的能力范围。
尽管巴里有自己的房子,但经济依然紧张。等孩子出生后,他们每年仅医疗保险就要多花6000美元。而育儿费用更像一个无底洞,比如令人咋舌的日托费用。
“生孩子的代价巨大,孩子会像毛毛虫一样,一美元一美元地把你挣的钱全吃光,就像艾瑞•卡尔在经典童书《好饿的毛毛虫》中描绘的那样。”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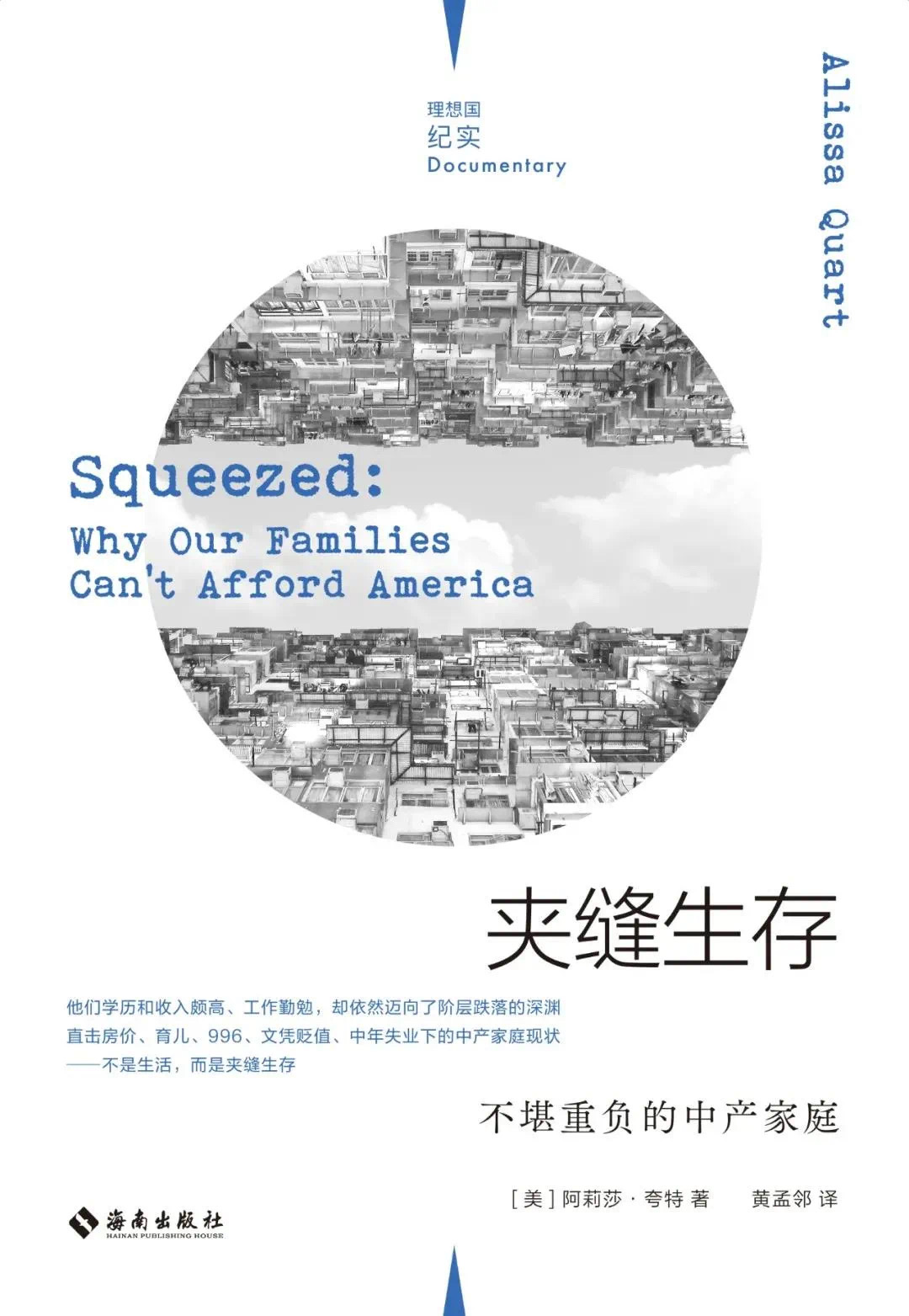
阿莉莎对此深有体会。正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才迅速意识到自己也掉进了中产阶级的下坠旋涡。
当阿莉莎在Facebook上发帖说,自己负担不起学者父母过的那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时,很多朋友都回帖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收入都交给了房东和日托中心,后者经常狮子大开口一般吃掉一个家庭30%的收入。

阿莉莎·夸特 图源Alissa Quart
阿莉莎和丈夫原本是自由撰稿人,但孩子出生后,他们开始寻找工作时间正常、收入稳定、提供医疗保险的工作。
阿莉莎发现自己当编辑挣回来的钱,先是大部分直接给了保姆,接着是日托中心。人到中年,她陷入了恐慌。
后来,阿莉莎到一家致力于报道不平等现象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担任主管和编辑。她也因此了解到有很多中产家庭都不堪重负,被生活追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其中不乏律师、教授、教师和药剂师等高学历人士。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所以它不仅仅是物质上,也是精神上的。

《东城梦魇》剧照
一地鸡毛的生活
巴里的故事并非孤例,像他这样的兼职教师很多,以至于优步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教师兼职司机的活动。
现实逼得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中产阶级的身份。
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
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成本在某些方面已经翻了一番。育儿是其中一项大支出。
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教育、玩乐等花费足以改变一名中产原本的生活方式。在美剧《欲望都市》中,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米兰达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单身时居住在繁华上东区的公寓中,结婚生子后出于经济考虑搬去了环境远远比不过上东区的布鲁克林,夫妻二人过上了手忙脚乱的双职工带娃生活。

《欲望都市》剧照
现实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埃米应该是城市的精英人士了。她在硅谷的科技公司做人力。她和丈夫的年收入加起来有15万美元。“在美国别的任何地方,这都是很大一笔钱了。”但他们的月收入的一半以上都交了房贷,儿童保育又吞掉了另外的30%。
埃米也要花很长时间通勤,因为公司附近的房子她都住不起。每天早上6点,她就开车带着孩子们出门了,7点把他们送到日托,8点30分到办公室,下午五六点接他们回家。“我每天花15分钟陪他们放松一下。”
但是他们又无法离开那些大城市,因为只有在那儿才有适合他们的工作。
他们也不敢轻易辞职,因为一旦离开职场,就会面临难以返回的困境。
塔玛拉·斯潘塞是一位50多岁的航空工程师,她一度放弃工作回家养育女儿。女儿上初中后,她想要重回职场,但是自己曾经所学的技术已经过时,无法再当工程师,只能寻找其他出路,比如学习网页设计或是专业烹饪。她因此需要支付额外的学费,背上高额的教育负债。
相比之下她父母的职业寿命要长的多,两位都是教师,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定期去度假,过着舒适的生活,更不必发展自己的第二人生。
在过去,一个人通常会在一个行业一直待着,第一份工作会带你进入第二份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人们一直做同一个职业,直到年满退休。
而如今“第二人生产业”火热。那些“第二人生产业”总爱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仿佛这些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者行动迟缓。
在美国,对失败的定义已经开始改变,“它代表着一地鸡毛的生活,而不必是一败涂地的生活”。
这些陷入困境的人们面对的不是一败涂地的生活,而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要像滚轮里的仓鼠那样不停奔跑的人生。
中产,只是他们难以为继、即将被戳破的一层泡沫。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5日,美国洛杉矶,学生和老师举行示威抗议美国政府削减教育经费。(图源视觉中国)
下跌的恐惧
在美国,没有隔代养育的习惯,所以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只能寄希望于日托。
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快成神话了。美国成年人现在平均每周工作47小时,还要面临突如其来的加班。高强度的工作需求使得父母照顾孩子成了一件难事,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极限日托因此而变得必需。
即使是小孩子,也要跟着大人永不停歇的工作节奏生活。一位日托园的负责人告诉阿莉莎:“十年前我们只做朝九晚五的日托,但现在商店都开到晚上12点,甚至24小时营业,他们需要我们。我们只能这样做。”
经济政策研究所对618个美国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在其中500个社区,拥有一个4岁孩子和8岁孩子的家庭所需要的儿童保育支出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房租均价。
安斯莉•斯泰普尔顿是一名40岁的会计师。她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或者日托。她计算照顾他们的费用占了她税后收入的87.6%。
“这让我有点想哭。”斯泰普尔顿对阿莉莎说。她曾和做公务员的丈夫讨论过应该谁辞职在家带娃,但他们都喜欢工作。
而在斯泰普尔顿的父母那辈,母亲在家全职照顾她,依然可以供她上私立学校。但在她这里,这个已经很难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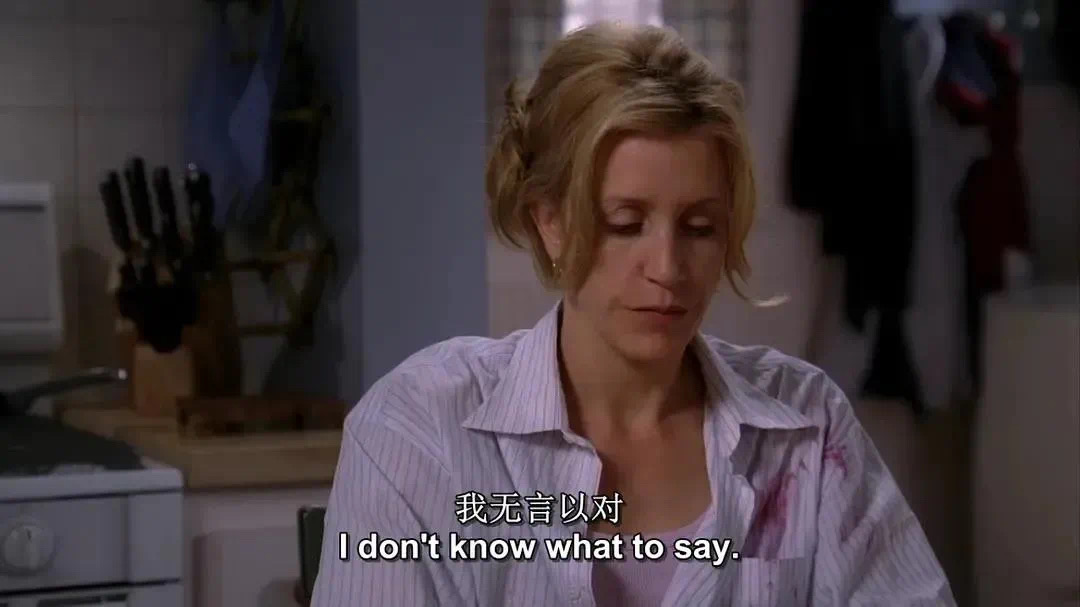
《绝望的主妇》剧照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中产阶级都在一步步滑向阶层掉落的深渊。
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所言,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在于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我们自己的阶级地位。
过去,中产阶级并不想追上极富人群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们觉得心安,但现在世道变了。
如今,中产阶级也在花钱聘请老师帮助自己的孩子与富裕阶级的孩子竞争。比如聘请数学老师的费用可以从每小时65美元至120美元,一直上升到每小时500美元。
这样的军备竞赛必然让中产阶级不堪重负。
贝拉米是一位人类学的终身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看着纽约上层阶级歌舞升平,听着他们谈论为了天才班测试给三四岁孩子请的导师,她咬着牙一言不发。
“我们所有可支配收入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了,”贝拉米说,“这说不上悲惨,但也令人感到劳累和厌倦。我已经很努力工作了,却没法喘口气。”
出路在哪里?
阿莉莎的一些朋友生完孩子以后,就离开了美国。他们搬去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儿童保育上,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比如在法国,政府提供了价格合理的日托服务,并对父母中有一位全职在家或雇用了保姆的家庭给予了税收优惠,还开办了接收3岁以上儿童的普惠性幼儿园。
现在美国也有一些城市开始推行普惠性学前班政策。纽约的“全员学前班”是成效最为显著的项目之一。在两年内,纽约的全日制免费学前班增加了5000个。
“我们很清楚学前班为什重要——一是它对儿童发展有长期影响,二是它会给支付幼儿园费用的父母带来的短期经济影响。”这项政策的设计者之一,理查德•比尔里对阿莉莎说,“如果一个家庭在儿童保育方面能够获得稳定的支持呢?他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了。”

《绝望的主妇》剧照
但目前,这样的学前班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依然是可遇而不可求。
而且,即使过了学前阶段,育儿期还有漫长的十余年。如果不止一个孩子,这个时间还要不断拉长。
真正的改变需要国家层面更宏观的行动。也许等待的时间要比我们这一代人育儿的时间还要久得多。
因此,阿莉莎给所有疲惫的中产家庭的第一条建议都是:不要责怪自己。
“我会告诉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而苛责自己的妈妈,你已经为女儿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说,你只是能力有限。为什么你的工作不稳定,而你父母的工作却不是,这后面有更大的原因。这是体制的失灵,实在个人层面之上的。”
一位妈妈笑着说,他们家的经济策略就是只生一个孩子。“孩子比较少,我们没有再次怀孕。”
这并不是一句俏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