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两点,刘玉珍坐在家里,面前架起一部手机。手机里,一场线上相亲会正在进行。主持人芝芝告诉她该上场了。刚开始,她有些紧张,讲话磕巴,声音颤抖,也没开摄像头。
刘玉珍看不见。手机安装了读屏软件,摸到什么就读什么,她靠声音摸索外面的世界。
“想象一下,有一种玻璃,有光,特别亮,”她说,“但是看不到。眼前白茫茫一片。”
如果她能看到的话,眼前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手机屏幕的上方是嘉宾的头像,左侧是嘉宾的交流框;右侧,观众的留言不断涌现,夸她声音好听。
这是一场在线直播相亲活动,参与者大多数是残障人士,从2020年3月至今年6月,已经举办了三场。活动参照《非诚勿扰》,前期报名、筛选,场上环节包括自我介绍、才艺展示、嘉宾答题、留灯、爆灯、提问、选择牵手,或者离开。嘉宾可以选择露脸与否,观众如果对哪位嘉宾感兴趣,可以在后台向工作人员索要对方的邮箱。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15岁以上未婚的残疾人数达到982万,占12.42%;初婚有配偶的占58.38%,而再婚率仅为2.44%,离婚率是为1.90%,丧偶率达24.76%。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群体数量庞大,且有持续扩大的可能,婚恋问题亟待解决。
自我介绍后,按流程到了答题环节,在一系列与婚恋相关的问题中,主持人问刘玉珍,最接受不了另一半的什么缺点?
“不被另一半接受甚至嫌弃,”她说,“最希望对方能接受不完美却真实的自己。”
刘玉珍的回答触动了即将上场的小太阳。
图 | 小太阳上场后,她的笑容感染了直播间的很多人
小太阳今年28岁,三年前从新疆来到北京,现在在一家外企公司工作。她性格开朗活泼,正如她坚持用的名字——“小太阳”,代表着阳光和生命力。
四岁那年,父母骑着摩托带她出门。一辆油罐车呼啸而来,司机酒驾,拐弯时油罐车车尾将他们甩到路基底下。爸妈受了严重的外伤,她的手被撞伤。
被送至医院后,医生全力抢救看起来情况严重的父母。休养了一段时间,爸妈基本痊愈。奶奶抱着小太阳,她却站不起来,腿跟面条似的。他们到乌鲁木齐检查,诊断结果是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全部瘫痪,从此大小便失禁。
在家乡库尔勒时,小太阳谈过一场网恋,那是在游戏里认识的男孩。对方是健全人,喜欢黏人,他们每天视频、聊天、玩游戏,小太阳把身体情况跟他说清楚,他说不介意。
后来她瞒着家人到广州找他,见面之前,男孩很兴奋。“他跟我说,要带我去这里去那里”,小太阳回忆,男孩儿把广州好玩的地方说了个遍。
她见到了真人,1米8多,高瘦的样子。但是,对方很失望,小太阳轻而易举读懂了他的表情和心思。当场分开,两个人没再见面。小太阳独自在广州待了一周,一个人去了广州塔和长隆动物园,之后丧魂落魄地回了家。
“现实和想象挺不一样的。”她说。
不被伴侣接受,是大多数残障人士在婚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甚至有时,家庭和社会也很难接纳残障的孩子。

谁来接纳他们?
刘玉珍模糊记得三岁那年,自己发了场高烧,然后就看不见了,是脑膜炎导致角膜溶解,她从此失去了视力。她还记得二奶奶整天说她:“你这个瞎子,将来谁会要你。”再大些,姐姐和两个弟弟去上学,她去不了。
童年的玩伴不多,刘玉珍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一起玩,她可以跳绳,靠绳子落地的声音和甩动的节奏判断进出的时机。爸妈外出做工,姐弟去学校,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她打开电视机,坐在凳子上,脸凑近屏幕。那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妈妈的嫁妆,成了她认识世界的窗口。听到有人回来,她赶紧把电视关了,爸妈心疼电费。
逢年过节或是外出,爸妈从不带着她——带一个视障孩子出行,不仅不方便,面子也挂不住。她连外婆家都没去过,外婆偶尔惦记她,从家里赶来看她。
图 | 刘玉珍渴望拥抱生活,拥抱爱情
刘玉珍讨厌安静,老鼠从家里的角落窜出,天上的鹰叫着飞过,常把她吓到。她喜欢夏天,听柔和的虫鸣鸟叫,也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身上暖烘烘的,心里也亮了起来。她有光感,能辨别白天黑夜,能察觉眼前有影子闪过,还能看到大体颜色。但是,她缺爱和安全感,“我晚上睡觉要开灯的。”郑重其事的语气,像是在描述一件很重要的事。
爸妈没怎么读过书,不知道该如何养育一个残障孩子,刘玉珍一个人在家待久了,会烦躁,砸东西。妈妈回来,动手扇她巴掌,爸爸也会对她吼叫,骂的话很难听,“嫁也嫁不出去,烂在家里吗!”很多残障人士都有类似的故事,有的父母甚至对孩子说,“很后悔把你生出来。”
女嘉宾之一的佳敏,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无力感爬满全身。
她今年28岁,现在广州生活。出生时窒息,腰部无力,站不稳,一直蹲着走路,如今坐在轮椅上生活。
“残障的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啊,”佳敏说,“父母应该教他们去坚强地面对世界,因为他们已经折了翼。”
走出家门,就该上学了。佳敏入学时,老师说不收,妈妈当场把她拉起来,说孩子可以自理;主持人芝芝的爸爸为了让女儿能有学上,把市里的幼儿园和小学跑了个遍,等她考上大学后仍然被拒;直播相亲活动主办方的创始人叫纪寻,她是腓骨肌萎缩症4型的罕见病患者,四肢因肌肉萎缩变形,她在南京浦口的工人大院长大,大院里的学校是职工福利,然而学校告诉她家,只招收“健康”的孩子……
上学后,同学的歧视、嘲笑又变成了成长路上的另一道坎。等好不容易毕了业,找工作也多是四处碰壁。刚到北京时,小太阳四处投简历,却总是石沉大海,难得有一个面试机会,只聊了10分钟,路上来回耗费了六、七个小时。芝芝北漂过半年,一次面试现场,面试官上下打量她几眼,委婉地拒绝了。
图 | 残障人士遭遇的困难多是常人难以想象
一个不太友善的循环已经悄然形成。据2015年新闻数据,残障人士普遍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文盲和半文盲占残障人士总数的16.35%,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总体的4.35%。残障人士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水平,经济水平又影响着恋爱与婚姻,以及接下来的漫长人生。
喜欢晒太阳的刘玉珍能够分辨冬夏阳光的区别,“冬天的阳光就是很暖,但是晒到的地方好暖,没晒到的地方好冷;夏天就不一样,周围都是热的,像一个热情的人。”
她渴望遇到一个热情的人,然而生活总是在泼冷水。

圈内特殊的择偶标准
“我是离过异的,这次相亲啥结果都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太大了。”刘玉珍有点低落,她今年37岁了。
现在,她在广东佛山做按摩推拿,手艺是在广西南宁的一家盲人按摩店学的,那里是她第一段婚姻的开始。
对方比刘玉珍大十几岁,是按摩店的技师,半盲。那时她患上胸膜炎,为了筹医药费,她以婚姻做交易,20岁时匆忙把自己嫁了出去。
“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把医药费还给他,能还多少是多少。”起初,刘玉珍是这么打算的。
但她把婚后的生活想简单了。与普通人的婚姻一样,残障人士的婚姻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但由于夫妻双方生理条件的特殊性,他们往往会爆发出特殊的矛盾。残障人士的婚姻状况比全社会平均水平差很多,据2015年新闻数据,他们的离婚率高出全社会水平一倍还多,达到了7.85%。
没有共同话题,刘玉珍和丈夫经常吵架。一年后,她生下一个男孩,“帮他生一个孩子,应该够了吧。”孩子1岁时,她找机会逃跑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清晨,丈夫接到客户的电话出去了。十分钟后人没回来。刘玉珍起身,翻找被藏起来的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没找到。她从包里抽了几百块,打了摩的到公交车站。下着小雨的路上,环卫工人在扫地,早餐小贩出来摆摊。
“如果有去南宁江南客运站的公交车,请告诉我一声好吗?”看不见的刘玉珍拜托卖早餐的师傅帮她盯着车辆。
“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是个男人的声音,按摩店里的同事,离过婚的三十多岁半盲男人,看见她出门,就一路跟着她。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男人说。
“神经啊,跟着我干什么。”
但他不管,一路跟着刘玉珍到了广州,慢慢地,她接受了他。
三年里,这个男人一直照顾她。“他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心情不好了就来骂我,觉得我是负担,说不该找我这样的人。”
分享起自己的婚恋经历,刘玉珍动了情,嘉宾和观众们也听得入了迷,但此刻,主持人芝芝却手忙脚乱,有的嘉宾准备的PPT里面的视频播不了,有的嘉宾突然放了鸽子,该他上场了,人却消失了。
6月份举办的这次在线相亲,报名人数是58位,主办方从中挑选了13位嘉宾。筛选流程很长,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情况,需要为残障者提供相应的无障碍服务。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自我介绍,怎么展示自己,需要工作人员一步步引导、沟通,过程繁琐。有的人第一次没选上,不甘心,会继续报名。
在芝芝的观察中,残障人士在闲聊中几乎都会讨论,要不要找健全人。本能中,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健全人当伴侣,“残障程度越轻的人,就越倾向于找健全人。”芝芝说。
这在残障人士的婚恋圈中,早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择偶标准。相比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学历、经济实力、家庭等方面的婚恋考量因素,残障人士则更多地围绕着对方的“残疾类型”,即“个体残疾情况因素”,这在诸多影响残障人士的婚恋因素里面,被赋予的权重是最大的。
较为轻微的残疾,或者对生活影响偏小的残疾比如聋哑,在这个群体的婚恋圈中更受欢迎,也更容易找到伴侣。宁波市某红娘团基于上百个案例总结出,精神残疾或抑郁症、智力残疾、失明、失去行动能力(比如依靠轮椅生活),是最难找到伴侣的四类群体。
如果可以,多数残障人士都希望能够与一位健全人士结为伴侣,但基于生活的现实及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大多数残障人士最终还是会与同一群体的人相结合。
但也有例外,这三场为残疾人群体举办的相亲会,就有听障的观众会关心,活动中有没有同为听障的人。

难过父母关
和第二任男友分手后,刘玉珍一个人在广州生活。
那时她已经和前夫办好离婚手续,在广州待得太久,想要换一个地方生活。一天,她去佛山某盲人按摩店面试,地铁站转线时,一个男人主动走过来问她,“需要帮助吗,你要去哪儿?”声音很年轻。
把她送上车后,男人站在刘玉珍面前,两个人加了微信。
他大刘玉珍四五岁,认识之后经常聊天,日子久了,刘玉珍察觉出了他的好感,但同时心生退缩。
图 | 刘玉珍到了佛山,辗转的人生,辗转的婚恋
不顺利的恋爱经历会加重残障人士的自卑心理,甚至对婚恋产生恐惧,刘玉珍坦言,“我们差别太远了。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原来,这位男士是广州本地人,毕业于名校,还在国外留过学,工作是做通信基站塔方面的设计。
但是,刘玉珍压制不住情感,“我迷恋他。”有一年,男人休了年假,带她去了青海湖。走累了会抱她,小心地呵护她,那次旅行,两个人在一起了。起初,刘玉珍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
刚开始,在这个男人面前,刘玉珍总是戴着眼镜,不愿意摘下。后来每次进门,男人都会帮她摘下,不自信慢慢地消失了。
某个雨天,他在办公室给她打电话,“你快走到阳台,你听雨声,伸手感觉一下,是不是冰凉凉的。”
刘玉珍照做了,“是啊。”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跟我交流。”她说。
后来,男人带刘玉珍见父母,父母完全接受不了:没有学历也就算了,眼睛还不好,还有离异的经历。母亲怄气到生病。他再不敢带刘玉珍回家了。
虽然两人没有分手,但心里有共识,他们可能无法结婚。
未来渺茫,刘玉珍常想要不要一走了之,但又放不下心爱的男人,焦灼且矛盾。
“想试试能不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她说这是她参加在线相亲最主要的原因。
主持人芝芝遇到过相同问题。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肌肉萎缩,她的右腿比左腿瘦。肢体障碍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时她拄拐出行,右腿没有气力,走路只能靠惯性推动力往前摆动,地面湿滑时,摔跤成了常事。
芝芝谈过几段恋爱,对方都是健全人。她认为,恋人的认可和接纳很重要。曾有一任男友跟她说,“我看不懂你们这群人,自己走路都不利索了,还要到处给别人搞活动,你们咋想的啊?也不嫌麻烦!你要是在外面磕着碰着了,我不在旁边,你说可咋整?”这些话,让芝芝听着不舒服。
她也遇到过家庭的阻挠,第二任男友的妈妈不同意,甚至这位母亲抑郁症病发,以死相逼。
“你能怎么说,肯定是家人重要嘛。”
最后,芝芝主动提出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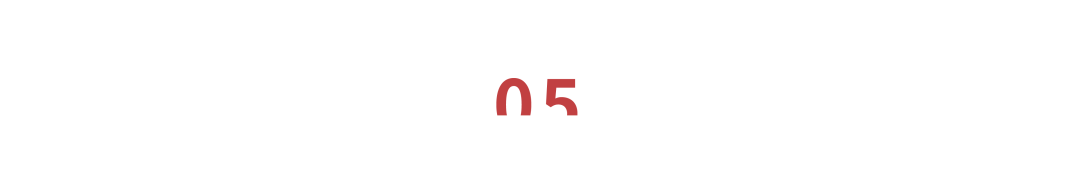
只要有他在,我就是幸福的
这三场在线直播相亲是由奇途无障碍发起并主办的,它是一家为残障人士提供旅游信息及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受损严重,很多线下活动也被迫暂停,为了保持社群的活跃,团队开始讨论策划新的线上活动。
咸鱼是团队里的文字编辑,留着小平头,浓眉,椭圆形的无框眼镜架在鼻梁上。他在山西太原,和家人住在一起,在家远程办公。17岁那年,一场病毒式脑膜炎袭来,他的世界从此寂静无声,也丧失了语言功能。
讨论中,咸鱼提议:“要不做在线直播的相亲活动?”
这句话,是冰倩和白衣爱情的起点。
冰倩是安徽合肥人,患脆骨症,即瓷娃娃。她两个月大时,医生下了判断,这孩子养不大,即便能治,也会活活疼死。她的头骨、锁骨、胳膊、手指头、鼻子、肋骨都折过。没有外伤,被肉包裹着的骨头在里头断开,一碰就晃,像一个提线木偶。
2020年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冰倩在相亲直播间当观众,白衣是场上的男嘉宾。场上有个女嘉宾贴出一张她和天天兄弟的海报合照,请大家猜她更喜欢谁。
白衣和冰倩的答案和理由一样:汪涵。因为她站得离汪涵最近。
此时的白衣人在大连,供职于一家IT公司。15岁那年,他突然感冒发烧,随后晕倒,转到市里的医院,昏迷了几个月。为了确定病因,他被推上手术台。没打麻药的情况下,医生划开他右腿根部的大动脉,将金属探头伸进去,原来他的左脑毛细管破裂,造成身体左侧偏瘫。
这场相亲会,白衣为女嘉宾留了灯,等结果时,身为观众的冰倩很紧张,“对方会不会选他啊?”最终,女嘉宾没有选他。冰倩找到咸鱼,表示想认识白衣。争得白衣同意后,两个人加了微信,他们天南地北地聊,很快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三个月的相处后,冰倩飞到大连,白衣去机场接她,紧张地握住她的手。
经过康复理疗,白衣现在只有左手不太方便,左腿可以正常行走,但有些长短腿,冰倩为他买了鞋垫,让他慢慢调整。
然而,双方父母都不同意。在白衣父母看来,儿子是一个健全人,不同意他找一个残障女孩儿;冰倩的妈妈希望女儿留在身边。老人们都希望孩子找一个健全人。
这对恋人很坚定,不顾家长反对,今年5月份,在一棵樱花树下,白衣向冰倩求婚成功,并于当月领证。
相亲活动结束后,小太阳认识了一个在广州的脑瘫男孩,他很热情,给她点喜欢吃的炸鸡,邀请她去广州潜水。“我可能不喜欢他。”小太阳写道,这段关系戛然而止。
佳敏注册了某交友平台,昵称是“轮椅姑娘”。她说感觉自己是一个异类,闯入健全人的世界,也有四五十岁的人来找她。她认识了一个聋哑人,但沟通不顺畅。后来,她注销了账号。
芝芝还在谈恋爱,她很希望进入婚姻,拥有稳定的家庭。
经历了几段感情的刘玉珍暂时看不清未来,她和那位广州本地男士还在处朋友,男士的母亲依旧不同意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平日里各忙各的,周末了他们俩聚在一起,走一走,吃顿饭,每当此时,刘玉珍就像个快乐的小女孩儿,无忧无虑的,“只要有他在,我就是幸福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纪寻外,其他名字为化名)
- END -
撰文 | 覃慧芬
编辑 | 张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