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监考人员和高校教练,修改考生答题卡,为了能让学生成功被名校录取,还将申请人的脸P到真实运动员的照片上来伪造运动员证书......
这就是2019年轰动一时的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人涉嫌贿赂,斥巨资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入学资格。
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他的女儿支付了75000美元,让她去一家考试中心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这里的监考员确保她获得需要的分数。
有个家庭支付了120万美元,以使耶鲁大学以足球专业新生的名义录取他们的女儿,尽管她并不踢足球。
……
这场招生丑闻引起了全美各界的强烈愤怒,但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更为深层的问题:在倡导“优绩至上”的社会中,到底谁才能成功,他们为什么会成功?
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书《精英的傲慢》中撕开了“美国梦”下优绩至上主义的暴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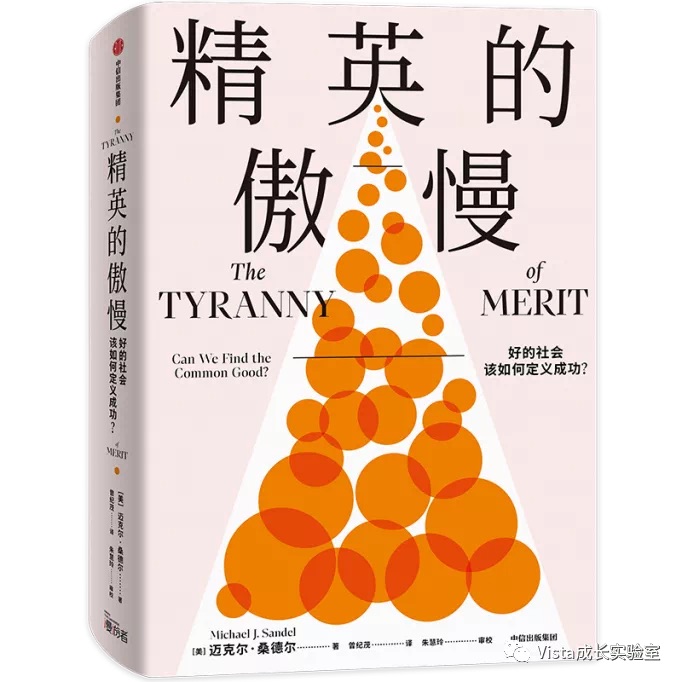
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也是哈佛第一门在网上免费开放的课程。他擅长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法,通过对极端假设或热点新闻的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公开辩论,被大众称为“一位有着摇滚明星般全球形象的哲学家”。
在美国想要进入常春藤联盟的顶级高校和在中国考入北大清华一样困难,而且越来越难。
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88年接受了大多数(54%)人的申请,现在只接受了9%。芝加哥大学的录取率急剧下降,从 1993年的 77% 降至 2019年的6%。
46所高校现在的录取率不到20%,这些学校中有几所就是那些父母被卷入2019年大学招生丑闻的学生的理想就读地。
只有4%的美国本科生就读于这些对学生极其挑剔的大学。超过80%的学生就读的学校录取学生的比例在一半以上。

抛开招生丑闻这件事本身,美国的精英父母们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
桑德尔在书中列举了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录取数据,这些高校有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中,来自全美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
读好大学越来越难了
桑德尔至今还记得他读初中8年级时的座位安排。
每次测验过后,学校都会大张旗鼓地公布成绩和排名,老师会按照学生的排名安排座位,每一次的座位安排都会根据最近的考试发生变动。
桑德尔的数学成绩很好,但并不是最好的,所以他的座位一直游离在第四张和第五张座位之间。
这是桑德尔第一次接触到优绩至上管理,14岁的他认为这就是学校的运作模式。升到十年级之后,同学们对成绩更加疯狂。“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数学最好的学生,谁在这个或那个测验中获胜或失败。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迈克尔·桑德尔
比起桑德尔考大学的上世纪70年代,考上好大学变得越来越难了。那时,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近1/3的申请人。8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大约1/5的申请人。2019年,这两所大学只录取了不到1/20的申请人。
而名校文凭显得越来越重要。奥巴马是优绩至上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不光是他和米歇尔,在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2/3的人都曾就读于常春藤联盟高校。
因此当谈及高等教育时,奥巴马认为大学教育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主要平台:“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应该决定你的终点。”
桑德尔发现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源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名牌大学的文凭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到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
因此,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海斯认为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这就使得文凭主义的傲慢成为了优绩至上傲慢的主要特征之一,由此造成的文凭主义偏见让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被自然淘汰。
一份在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人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列为最不受欢迎的群体。不光是精英阶层对他们存有偏见,这个群体本身也接受这份偏见,认为走到如此地步是自己的原因。
富人为了入学,无所不能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提出新的观念:精英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可以成为社会领袖。科南特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为公立学校的天才学生设立哈佛奖学金,根据智力测试对他们进行筛选,而这个测试就是“一战”期间军队使用的方法——SAT,现在通常被称为“美国高考”。但是新的情况出现了,SAT是可以进行辅导的,这就使得富裕家庭可以提供底层家庭提供不了的教育优势。总之,这些孩子们大学前的学生时代也是在竞争激烈和高度焦虑中度过的。桑德尔在书中援引资料表明,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你的家庭收入越高,你的SAT分数就越高。在收入阶梯的每一个层级上,SAT平均分都会增加。在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入学申请中,SAT 分数差距尤其明显。如果你来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那么你得分超过1400 分(满分1600分)的概率是20%;如果你来自贫困家庭(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那么你的这一机会是2%。绝大多数得分高的人的父母也有大学文凭。在曼哈顿等地,一对一指导的收费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家长们还会安排琳琅满目的德智体课余活动包装孩子的简历。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私人招生顾问的建议和指导下开展的,这些顾问的费用可能超过耶鲁大学四年的学费。一些顾问还会建议父母为孩子找人开具残疾诊断证明,以让孩子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额外的加时。(在康涅狄格州郊外的一个富人区,18%的学生得到患有残疾的诊断,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6倍多。)另有一些顾问专门设计定制的暑期国外旅行计划,旨在为大学申请论文提供令人信服的素材。18世纪西方社会阶层金字塔,今天处于顶层的精英阶层,中下阶级依然无法触及近几十年来,随着大学录取的竞争加剧,辅导和备考已经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在这样新型的教育军备竞赛中,桑德尔认为“直升机式育儿”的富人父母始终占据有力的一方,也可以顺利地将上一代的特权传下去。“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中小学教育的不平等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在学生申请大学的时候关注教育不平等的话那就太迟了,这将永远无法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得早点开始。”桑德尔说。1976—2012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5倍多。随着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充满焦虑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成了常见的痛苦。《时代周刊》指出,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童年的征程现在很早就开始了。“在6~8岁的孩子中,自由的游戏时间从1981年到 1997年减少了25%,而家庭作业增加了不止一倍。”桑德尔看到了他的许多学生挤过千军万马上了名校后依然在追求绩点,而无法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不管是成绩还是社团,学生们都削减脑袋证明自己可以挤进这些低录取率的精英团体。这又让高等院校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高校的资格认证功能开始膨胀,甚至要压倒其教育功能。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而且,他还发现学生中“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数量惊人”。
21 世纪初,在加州旧金山郊外的一个富人区治疗年轻人的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注意到,许多来自富裕家庭、表面上很成功的青少年其实非常不快乐,与外界脱节,缺乏独立性。“拂开表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沮丧、焦虑、愤怒……他们过度依赖父母、老师、教练和同伴的意见,并且经常依赖他人——不仅要给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还要使日常生活顺利进行。”
莱文开始意识到,父母的过度管控是这些富家子弟们不快乐和脆弱的主要原因。
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高危青少年”。尽管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优势,但在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群体中,他们患抑郁症、滥用药物、患焦虑症、患躯体疾病和感到不快乐的比例最高。
哈佛大学的招生网站上二十年来一直挂着一篇研究文章,作为警示。他们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里取得了亮眼成绩的人,最终会成为“集中训练营里浑浑噩噩的幸存者”。
在桑德尔看来,教育不仅仅是让人们为工作和经济做好准备,教育也是为了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和妻子琦库·阿达多曾出版过一本童书《巴巴央和魔法星》。他为这本童书设计了N个问题。“夏玛贝玛的动物们有一条特殊规定:禁止互相捕食。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规定‘禁止互相捕食’?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咕咕嘟告诉巴巴央,他们有‘禁止互相捕食’的规定,因为‘那会带来许多仇恨怨气’。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会带来‘仇恨怨气’?什么样的规定能帮助人们改变对彼此的感情?”这是他和妻子给两个儿子编的睡前故事。这种不断诘问的方式也是他们家的日常。他们希望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中国演讲时,桑德尔曾发现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焦虑:我的孩子能不能有与众不同的独立思想?“在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教育环境下,孩子并不是特别被鼓励过分独立的思考,而我出于一种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在老师眼中变成一个‘刺儿头’,所以我的问题是,怎样既让他保持我追求的那种永远独立的思考,但又能够使他在学校保持一定的安全性?”一个妈妈忧心忡忡。这样中国式的问题让逻辑缜密的桑德尔也有些答非所问了:“我想任何一个国家所谓的德育体系,都应该鼓励儿童和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