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公布过一个数字,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占了7.2%。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规模接近800万。
基于我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较多,所以经常能够跟小区里的老人们打上照面。在某个非周末的上午,小区的广场上也许有二三十个孩子在玩。一般来说,孩子的看护人中,老人占三分之二,妈妈或保姆占三分之一,爸爸则基本只有我一个。
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担心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一个大男人,不好好上班去,过来带什么娃?”但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我逐渐发现了育儿群体中存在一个轻微羡慕链:老人对保姆比较不屑,却羡慕妈妈带娃,而妈妈则和老人一起羡慕爸爸带娃。

不管是鄙视链还是羡慕链,相关分析暂且按下不表。回到开头的数据,由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较窄,所以,我相信从跨区域照顾晚辈的流动老年人的实际数量,应该不止800万人。这点数量,可能还不够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分的。
在与这些老人的接触过程中,我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他们的一些无奈和怨气。老人聚在一起,话题很容易引向对子女的吐槽,这一点,如同每一个妈妈群里永远都不会缺乏“吐奶”(吐槽孩子的奶奶)的声音。
无奈和怨气能够被说出来,也许情况还不算糟糕。麻烦的是老人不知道怎么抱怨,该对谁抱怨。基本上,老人对子女肯定是三缄其口,不会轻易表露出真正的想法。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访谈,发现子女普遍容易对老人的承受力持乐观态度。
但事实上,这些老人们的诉说空间极为有限。有媒体甚至用“子女身家上亿,但他却常常失眠,甚至哭到天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内文讲的正是老人照顾孙辈不被理解的境遇。
媒体把这些为了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人称为“老漂族”。老了还漂着,我觉得挺形象。的确,他们在大城市里没有根,也没有能力扎根。而他们的困境只有一些零星的新闻报道可以呈现,例如频发的抑郁症,患上早发性老年痴呆症,不过,接受采访的常常是觉得有愧于他们的子女,并不是他们自己。可见,他们的话语权是多么羸弱。
中山大学的钟晓慧博士曾在“全面二孩”政策颁布后,撰文呼吁“重视‘全面二孩’政策下老年女性照顾者的境遇”,不过由于这个群体太过边缘,相关的调研资料很少,因此能够改变的并不多。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公共政策对全职妈妈的照顾都远远不足,对于奶奶、外婆这样的“老漂族”又怎么可能出台什么政策呢?

不自由和无社交
这个月初,我的孩子刚过一岁半。2017年的后半年,我母亲也曾做过“老漂族”——她从老家县城赶到广州,帮我们一起照顾当时不足半岁的孩子。因为妻子全职在家,我的投入也不少,所以母亲到广州后,只负责买菜、做饭和搞卫生,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不用她管。她的腿脚不太好,住在五楼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让她抱过孩子上下楼。
但是,即便对她有相当照顾,中途还带她出门游玩了几天,在我给她订了回老家的车票之后,她还是明显表现出了一种解脱感和兴奋感。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我的同学在上海,她的母亲最近挺开心,原因就在于确定5月底会由孩子的奶奶来接自己的班,这意味着她很快可以回到山西老家去了。我的一位堂亲在宁波,他的母亲过去帮忙,也适应得非常艰难,一回到自己的小山村,精神立马好了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导致这些老漂一族痛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太辛苦吗?也许是的。毕竟很多家庭中的老人,既要带娃又要做家务,晚上可能还要哄睡。一天下来,老人很难有长段的休闲时间。但辛苦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母亲告诉我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
对于很多老漂族来说,他们被动实现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而这个转型过程充满了艰难。比如卫生观的冲突,他们可能觉得奶瓶没必要每天专门消毒,会质疑几件单衣为什么要用洗衣机,会认为洗碗机毫无用处浪费钱等等。每一个细节她都需要适应,每一样电器都在改变她的认知,同时也在削弱她的重要性。
大城市的出行也是一个问题。在小镇生活的母亲出行便利,因为全镇就几路公交车,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走路直达。但到了广州,小区坐落在郊区,正所谓小区的围墙内像欧洲,围墙外像非洲,出个小区得刷两次卡,去稍远的地方要么打车,要么搭地铁。所以,用不了滴滴打车,也不敢一个人搭地铁,更看不懂手机导航的母亲,生活空间就被固定在了小区内。
此外,老漂族中不少是小镇上的知识精英,当过学校老师,或者是基层干部。这些曾经颇受学生爱戴、下属尊敬的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们,也许拥有比我母亲更强的出行能力,但是介入育儿的过程还是会让他们鸭梨山大。毕竟,两代人,两种育儿方式,情形早已千差万别。
例如,婆媳关系有一颗不定时炸弹,当媳妇指出婆婆某一点做得不够科学时,婆婆会习惯性地反戈一击:“我当年就是这样把你老公养大的。”此言一出,必定引发世界大战,一脸懵逼的丈夫往往不得不介入调停。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一代年轻妈妈们与过去的妈妈已经截然不同。女性长辈提供的许多经验,都被年轻妈妈们毫不客气地看作是伪科学、谬论和糟粕。取而代之的是读过大学甚至是研究生的妈妈们搬出的“科学育儿宝典”。
在科学育儿宝典的指引下,育儿不可逆转地变得更加精细化,从辅食搭配到睡眠训练,从尿不湿使用与括约肌发育的关联,到婴幼儿的安全感如何增强。老漂族们需要将自己过去的育儿知识体系推倒重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很难有能力重建体系。
日常生活中,年轻子女们的批评、夸奖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权力,左右着长辈对自己育儿能力的再判断。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权力分配规则,年纪越大,育儿经验越丰富,实践中也就越权威。但现在,情况被彻底反转,老年人成为落后的、无知的、愚昧的,他们的付出被轻视,他们的观点被边缘化。
一方面是巨大的付出,另一方面则是先前权威的丧失,这个过程必定伴随着让人抓狂的摩擦。例如,年轻妈妈们所发明的“有一种冷叫作奶奶觉得你冷”,看起来是对奶奶育儿的一种调侃,但在实际育儿过程中,因为孩子应该穿2件还是3件,由此引发的家庭战争还少见吗?
付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被认可。不被认可也就算了,可怕的是还没处倾诉。老漂族面临的正是付出之后不被认可,并且无处可以倾诉。这又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我曾鼓励她每晚去小区的广场跳舞,无奈她表示并不能真正找到“合心的人”。语言不通,交流就不够顺畅,很多心理话是需要家乡方言才能表达的,普通话的功能仅限于信息交流,而非情感交流。

从千里之外赶来,这意味着与原先的社交圈隔绝。但社交的作用常常被子女们所忽略。事实上,家庭内部永远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这些矛盾如何被消解掉。社交圈、老闺蜜的作用,其实就在于消解家庭争端带来的父母情绪。通过对外吐槽,老年人获得了一种情绪上的平衡。反过来,假如一个人的社交需求长期无法满足,患上精神类疾病的概率就会大增,由此引发的痛苦将加倍涌来。

奉献的成瘾性依赖
不自由、无社交,成了“老漂族”的痛苦来源。然而,都这么痛苦,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长辈愿意跨越千里前去给子女照料孙辈呢?
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一种根植于熟人社会的“面子”观念。举个例子,子女在大城市买房、安家、生娃,身旁的人都夸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这时候,如果自己没能去参与建设子女分小家庭,没能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被召唤去帮助他们,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异地照料固然可能存在各种不适应,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愿意分享其中的乐趣。在长辈的社交圈中,为生育初期的子女提供帮助,既是一种为人父母的义务,也是一种跟随家庭腾飞荣耀。更何况,即使有什么不快,孙辈一声甜甜的叫唤,就像一针麻醉剂,可以将老人们的痛苦暂时冻结。
不过,相比“面子”因素,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代老人所普遍具有的奉献精神,或者说是他们奉献成瘾特点被最大化利用了。奉献成瘾的本质是独立性的丧失。一个人只能通过对家庭不断奉献,才能获得自我认同,这就是奉献的成瘾性依赖。
举个例子,很多老人在帮子女带完第一个孩子后已经觉得很辛苦,奈何“全面二孩”政策一出台,想着可以多一个后代,又一头扎进育儿的深渊里。这里存在无奈,也存在同情,还存在期待。无奈自不必说,同情主要是对儿女的境遇知根知底,明白一旦自己抽离,受苦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重点可以说说期待。期待常常是子女传递给长辈的,一些夫妻双方都很忙,事业上不断走高,照顾家里的时间也被不断压缩。在这个时候,较高物质回报会变成一种新的动力,让老人觉得这就是好生活的形态。尤其是小夫妻都忙于工作,老人自己育儿的权限大增,对于到底该怎么育儿可以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操作。所以他们会觉得相对自由,也更有奔头。
但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底色就是焦虑的颜色。在无比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那些只顾着自己赚钱的父母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父母”。所以最终一定会有一方(往往是妈妈)回归家庭,开始强势介入育儿过程。在这个时候,代际育儿合作中该有的冲突,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80后可能是集体喊出“父母皆祸害”的第一代人。但在婚恋、工作层面不堪被父母控制的这一代人,却很可能在育儿上毫无节制地使用着父母奉献成瘾的特质。因为那些对子女横加控制的父母,反过来也特别乐意为子女付出一切。
不论控制还是付出,实质都是缺乏人生的独立性。这些父母需要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依附在子女的新家庭上,才能感受到生命的脉搏,而一部分曾经敌视父母的80后,他们也并不能选择一条高晓松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路。秉持憎恨还是选择索取,最终得看他们的利益和方便,而不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男性的习惯性缺位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于,父母这一代人除非病倒,否则很难开口说“坚决不给你带娃了”!所以,在沟通、安排层面,基本格局对老漂一族很不利,他们生命的余热被子女不断征用:养老钱成了子女新房的首付款,退休后闲适的生活变成每天打仗似的育儿过程,曾经的兴趣爱好被迫收起,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圈里每天几段的孙辈小视频。

不客气地说,许多家庭的育儿过程,实际上相当于年轻夫妻对老年父母的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自然伴随着各种冲突和反弹。婆媳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冲突的主要形态。媳妇儿说婆婆如何糟糕,婆婆抱怨媳妇怎么强势。从表面看,家庭矛盾的来源主要出现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互不相让,各自任性,让作为丈夫/儿子的男性极为难堪。
但事实上,婆媳双方恰恰是整个社会和家庭结构里最弱势的两个角色。男性在婆媳争吵中呈现出的窘迫与无奈,是以自身在育儿中实质性缺位为前提的。
换一种场景描述,假如男性能够承担起一部分育儿责任——其底线标准就是能够独立带一整天的娃,负责娃的吃喝拉撒睡全套流程。那么,男性首先可以弄明白双方争吵的点在哪,其次可以有能力进入争吵的情绪状态,最后还有能力把具体的育儿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婆媳争端即便不能扼杀在萌芽阶段,起码也不会扩大化。所以,回到开头的羡慕链,爸爸育儿之所以更受褒奖,原因大抵就在这里吧。
在许多城市中产家庭,男性育儿的参与度正在加强,伴随着男性投入的增加,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内部沟通成本更低。作为老人,他们扮演的不是日常的照料者,而是偶尔陪伴的家族长辈。所谓“含饴弄孙”,本意是自己一边吃着糖果,一边逗着孙辈玩。但我们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如果每天都要照料孙辈,还要承担做法打扫的家务,也就很难有空闲和心情一边吃糖一边逗孙辈了。
男性在育儿中的缺位是一个“千年痼疾”。如果不是男性在近几十年遭遇了女性与职场崛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男性的觉醒还很遥远。有关男性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代加入深度育儿的队伍,具体可以阅读我在大家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为什么爸爸应该深度参与育儿》。

隐性的剥削手段
而除了男性在育儿上的缺位之外,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缺位,是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即使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做得最好的上海,政府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育服务。最新的上海市完善幼托服务的文件中,依旧还是鼓励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幼儿托育。以家庭为中心当然有很多好处,爸爸妈妈自己带的孩子通常比保育员照顾的孩子更活泼聪慧。
但是,国家理应提供6个月之后让孩子进入公立托儿所的选项(具体可参见德国和日本的做法)。选不选是一回事,有没有是另一回事。只有这样,才能部分地解放女性,也部分地解放老漂一族。
没有公立保育机构,或者说政府鼓励家庭式的育儿,那么就应该在税收制度安排、育儿补贴层面基于一定的优惠。但现实的情况是,像我这样全家三口人只有我一个人有收入,另外还房贷的家庭,没有享受到任何实质性的税收优惠。
客观上,不公平的制度挤压了女性的就业机遇,而由此获得更多更好工作机遇的男性,也因为承受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参与育儿。
而在男性产假方面,江苏省因为提供了15天的男性产假,被媒体大书特书一阵子。15天能做什么?参与过早期育儿的人都应该明白。如果不能延长男性的产假,男性就更加没有时间参与育儿。女性的育儿压力就更大,老漂族的数量也会更多,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回到男性在育儿中的缺位问题,祸根也有制度安排一份。
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最终导致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年轻夫妻必须向家庭内部整合资源。远在农村或小镇的老人,既省钱又不存在身份信任问题。所以,年轻夫妇对长辈的征召,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在势如破竹的征召浪潮下,一部分原本不愿意进城帮子女育儿的老人,成了没有道德的人。舆论会给他们洗脑,会曝光他们的羞耻感,最终会催促他们走进城市,走入子女的家庭。
但实际上,这锅又不能完全由子女来背。因为这等于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来迫使城市年轻的夫妇以代际育儿合作的名义,向乡村老年的父母进行剥削。某种意义上,这种剥削因为融进入了家族情感的脉络,变得极为隐性。相比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样的显性剥削手段,隐性的剥削更深入骨髓,所造成的社会创伤更难疗愈。
对于50、60后的老漂族来说,在青春时代饱受疯狂社会运动创伤之后,在老年阶段也未能免除被隐形制度剥削的结局。这不得不令感到人唏嘘:命运对他们实在太不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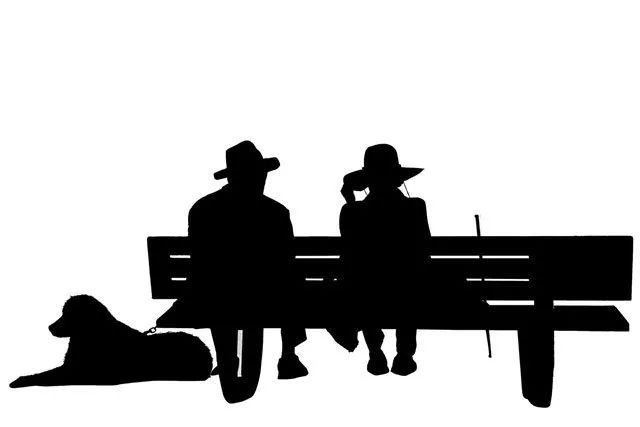
更吊诡的是,造成目前老漂族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其次才是爸爸育儿的不足,最后才轮到他们本身的学习能力欠缺。但在现实中,老漂族所承受的指责和压力最大,极少参与育儿的爸爸也只是偶感内疚,未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则毫无愧色。责任倒置的情形,褒贬的错乱的现状,或许正应了那句俗话:这个时代,老实人最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