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曹东勃
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貌似不言自明、多此一问。因为大家就是通过一路读书和应试才走到今天的。可是进入大学之后,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选择机会,读书还是不读书,这样读书还是那样读书,终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高尔基的那句老话已经被说烂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什么呢?至少在信息革命之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书籍都是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物质载体。语言、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极大地超越了其早年的幼稚阶段——在那个时候,人的基本生存高度依赖于当世经验的口耳相传。对农事的每个环节、对节气规律的把握,离不开长者的智慧,老年意味着丰富经验的显现,老年人受到社会的重视,晚辈向长辈学习,这样的文化叫做前喻文化。有了文字、有了印刷术把经验和知识物化为白纸黑字的物质载体,一个人就有了通过阅读增长知识并获得解放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可以替代老师,反过来则不行。即便老师都死光了,只要有书,人类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就不会中止。
有一副著名的楹联:“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爱读书是人品好的象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推崇“耕读之道”。所谓耕读,字面上来理解,无非是耕作和读书。把它引申到当代,就是保持自食其力、满足基本生活开销之余,还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给其兄弟所写的家信中比较了四种家庭类型,殷殷叮嘱他们要谨守耕读之道,他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曾文正公说的很明白,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的底蕴,官二代、富二代都很难走得长远,不如耕读孝友之家。
可是,学问之道,本来就不限于读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德性修养、内心开悟、艺术灵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都未必要依赖于读书这种间接知识。就自然科学来说,观察、实验的重要性也似乎远胜于读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呢?
对于这个问题,唐君毅先生提出了三个理由:
其一,书籍是前人探索和理解世界的记录,承载着文化的积淀。我们生于已有书的年代之后,唯有通过书籍理解人类文化之镜子,然而却是整个人类文化之镜子,由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之世界。
其二,读书可以增加我们思想的广度。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面小镜子,而读书,就是把我们的小镜子,面对书籍之大镜子,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新去映射古往今来无数聪明智慧的心灵所已经洞见的现象与真理,将之照入我们的小镜子中。
其三,读书可以增加我们思想的深度。对知识和思想的反复咀嚼、品味、吐哺,这一知识和思想的绵延和再生产过程,将我们心灵这面镜子转变为凹凸镜,使我们聪明和智慧的光辉,既能像显微镜那样洞察秋毫,又能像望远镜一般望穿宇宙,从而体会到更细微更深远的自然、人生、社会的各种现象与真理,由此,锤炼出思想之纵深。当我们阅读前人时,我们的心灵是凹镜,从四面八方发散地获取历代中外先贤的广博智慧;当我们传诸后人时,我们的心灵是凸镜,将自己毕生之所学所悟聚焦于一点,为知识的累积增长贡献绵薄之力。
蒙田说:“初学者的无知在于未学,而学者的无知在于学后。”第一种的无知是连字母都没学过,当然无法阅读。第二种的无知却是读错了许多书。这种无知的阅读者,我们通常称为书呆子,虽广博而实不通。希腊人给这种集阅读与愚蠢于一身的人一种特别称呼,这也可运用在任何年纪、好读书却读不懂的人身上:“半瓶醋”(Sophomores)。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以为读得多就是读得好,所谓贪多嚼不烂。阅读也好,学习也好,要在得法。方法至关重要。
前面讲了大半天方法,并不是要故弄玄虚,也不是要讲多大的道理。想来身为一个读书人也已有些年头了,向以阅读为乐,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困惑、体验和教训,总结经验完全是个体的事情,但是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共鸣,提供一点参考,故而整理出几条读书的体验。没错,这里只能用“体验”二字。

第一,读书为自己。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翻成白话文,大约就是一种兴趣导向型的阅读。读书要有选择,有比较,有次序,有目的,因为人的时间是稀缺的。但千万莫忘一条根本原则,读书是为自己读,是为满足兴趣而读,是为精神愉悦而读,不是为人前炫耀来读,更不是为积累谈资来读。为知识而知识的习惯,本非我们的传统。实用性极强的特征使得难以脱离器物层面进入思想殿堂,更乏严谨逻辑体系。诚然搞学术的必要条件是要有闲,但同样有闲,中国学人却未如海外学人那样出产系统性的成果。这却是需从读书阶段就有必要严加注意的。
第二,读书如吃药。书能教给你很多事理,书是良药。但是药三分毒,是故书亦有毒。有人不喜欢人家读书,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反动。这话本身也很反动,但在某个特定角度来理解,也有其道理。读书若不以其道,则无异于食毒也。《天龙八部》里扫地神僧是怎么批评鸠摩智的?他说鸠摩智从一开始就迷恋玄而又玄的武功招数,已然入了魔道且越陷越深。扫地僧慈悲为怀,便在他每次所窃上乘武功秘籍之旁放一部法华经。老人家的意思是什么呢,两类完全不同的武功药性相冲,可以克制单方面增长的魔性。

实际上我们读书也要如此,很多书是很高深玄奥富有吸引力的,但长时间浸淫于一类书籍,尤其是某些玄奥的书籍以及某些学派,毒性特大,人就会走火入魔,以至于影响日常的心智和行为。一个小药方是:兴趣多元、类别对冲。一定要互补,每看一本玄奥的书之后,再看一点务实的、操作性的书,让大脑回归真实世界中来。
古人讲的“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也是类似的意思:精神和思想状态好的时候,心气刚强、牢骚满腹的时候,要静下心来读理论性强的书;反之,当情绪低落、精神萎靡、昏昏沉沉的时候,要翻阅历史,从中激发奋斗的信念、重拾恢宏的志气。如此一张一弛,经史互参,心性会更平和,走得会更长远。
第三,读书贵整体。有的读者看书有猴急的毛病,要不得。读书不看序、译序、前言、导读、目录、后记、译后记、跋,逮到一本就直奔主题,这种叫做囫囵吞枣、欲火中烧。要先好好打量打量,从前言中知道作者选题的背景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从目录中大致看到作者论述的逻辑结构,这样读书才有目的性——读书必须要有目的、有选择,因为时间太稀缺了。有的人博闻强记,但也仅此而已,不能融贯,不能“吾道一以贯之”,没有一条能把散钱穿起来的钱绳。初则读书时可能由于学术术语、背景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准备不足的缘故,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我称之为“文献学准备”的阶段——即对于所要了解的领域的人物、论题、争议、历史演变了然于胸。一旦过了这一阶段,就应该跳出部门的困囿,整体观之,约之而后博。
初读书者最忌讳的是被一本书中庞大的旁征博引所震慑,也许在著者而言这只是为论证缜密而作的必要的文献描述,而部分学者也特别有一种我称之曰“脚注实体化”的偏好,好好的话本可以放在正文之中他偏要在脚注中大幅度展开以至于占据一页纸的大部分篇幅,读者最好不要被这些表面上庞大的枝节性部分所纠缠。以自己的思维理出一个头绪,用自己的话能够简述一遍作者的框架和逻辑,就算读懂了。这也很像有些数学题,你解出来以后一定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对是错,有些题目就不能。
我在大学时就有一个习惯,听讲座、整理讲座的内容尽量不用录音设备,当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表述别人所讲的故事时,你可能比机械地做录音机的奴隶要更好,也更能理解作者的意思。这里特别推荐贺麟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在重庆给一些年轻的学生们的一篇讲演,题目叫《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这篇文章我是大三时读到的,解答了我很多方面的疑惑,很有助益。
第四,读书要准备。有一两年是要做准备的,这个时候不懂得古今中外学术界里有哪些人是重要的,哪些书是经典的,所以买书、借书都不得要领。我把这叫文献学的准备。
有这一两年的积累之后,自己想研究某个领域后,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查阅。也学会了鉴别书的好坏优劣,这样读书不会走冤枉路,买书也不会花冤枉钱。
从这个意义看,学习任何一门学科之前,首先了解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也就了解了这门学科的人物传记、文献史,实在是至关重要。数学史、科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等应当具有相应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学生据此各取所需,攀爬参天大树也就方便得多了。学习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读史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此外,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兴趣,重点关注若干出版社,一些有历史传承的出版社是有着自己一贯的偏好的。对于处于读书初始状态、知识积淀还较低、选择和鉴别的能力还不够强时,信赖一些出版界的“百年老店”是风险规避者的理性选择。
第五,读书有规划。读书究竟是起步于厚还是薄,因读者而异,因话题而异,也因著者而异。比如一般人读哈耶克,很容易从那本薄薄的《通往奴役之路》开始,通俗易懂;但其实也可以从《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开始,也可以从《致命的自负》开始,这都说不定。而厚的书,未必都是难读的,比如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大卷,其实内容很有趣,学术之余不仅详尽梳理各流派的演变,也有不少学术八卦充为调剂。关键是要有规划,有链条,尽量不要四处出击,多线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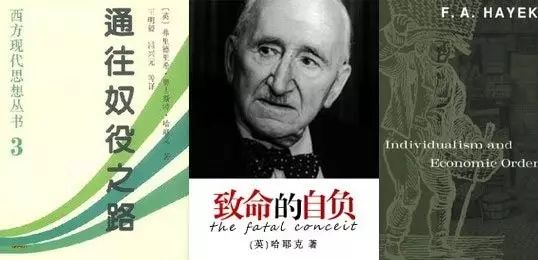
厚薄之辩倒在其次,首先是要确定方向和题域。由于有一个主攻的导向作为标杆,围绕这个中心吸纳一切相关学科的知识就很有助于转化为自身的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行动,反之,就变成成语接龙和术语大串联。因而必须要有自己的转化和理解,而不是单单地读一本书,就堆砌一本书的概念;读几本书,就串联几本书的术语。读书的目的是借鉴他人的思路,锤炼自己的思维,而不是变成“读书学“的研究者。这种锤炼思路的最好办法是用你自己的理解和逻辑来重新给书编码、排序、归纳,“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所指的就是读了很多书却只能“报书名”做泛泛之谈而无自身理解的典型的“书呆子”形象。新时期的人,尤其要注意不成为书的奴隶,要自己驾驭书,而不是被书所驾驭。
消费时代、消费社会,读书作为一种消费,是个人的事,没有人强迫读书人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人指望读书人个个都成学者,所以大可不必自加压力。出现以读书谋生的阶层,首先当然是文化开始发达的标志。但还需避免舍本逐末,听闻一些书评人压力颇大,以至匆匆急就尚嫌不足,还要委托他人代劳。为读书所累到如此地步,可真称得上是读书的异化了。
我很喜欢读方家的书评,那绝不同于一般,不是八卦罗列、背景介绍、章节扫描,而是有自己的逻辑和思考、追问和探究,是带着问题进入书中而又带着问题走出书来的。比如当年张维迎教授《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出版后,韦森、姚洋、郑也夫等学者分别做了长篇书评,每篇各从自己的关注点入手,有的放矢,张氏也颇为赞赏并将之列入再版附录。这样的富于逻辑性的书评读起来能给人顺畅、清晰、物超所值之感,远非一夜之间就可提笔挥就的随感所能比拟。
第六,读书做笔记。经典之作读过以后应当整理读书笔记。欧阳修说读书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这说明要学会甄别书的重要程度,并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读书笔记也是这样,那些最为重要、经典的书籍,不仅是需要在书旁钩钩划划、写写记记,还应该整理自己的感想。读书笔记可以人物为主线——读一著名人物的多本著作,比较其一生思想变化的过程;也可以就事论事,单就一本书、一个话题整理。
读书笔记的写法,首要的是要写出该书的独特之处,在此前提下,再求全面。有些书籍只有个别篇章精彩,那就可以只针对这些篇章来写。在描述作者的观点之余,也应有自己的解读。学会用大书指导小书,以一本书分析另一本书,用具有普遍意义的讲方法论的书解读具有特殊性的专题书,用经典书比照前沿书。用基础的书指导专门的书,所以基础必须先行,先通再专。否则连流派的先后演变还没搞清楚,连人物思想之间的联系还不理解,就看专门性的书,那会很吃力,遇到很多术语很多背景很多人物和学派就会不懂,上下文也会看不出。
第七,读书莫迷信。书单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文献检索的提要。之所以要有开书单的人,就是因为初入门者需要在不断磨合中提升自己鉴别书之优劣的能力,逐步对自己所熟识的几个领域里有影响的人、有影响的书以及有影响的人写的有影响的书中的代表作了然于胸。当然未必都要读完,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都读完——即便是一个学问中人,一辈子能把一个值得研究的人或问题搞深搞透也已不简单。但至少当他(她)想要检索的时候,头脑里会有一张简明扼要的清单。一旦进入轨道之后,就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阅读,而不应该被庞大的书单吓住。头脑中要有一个目录,查哪个方面要找哪些人,了解他(她)的哪些东西。书单是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一定要自己掌握,最后做到自己能够给自己开书单。
第八,藏书非摆设。书籍是物品,更是商品,所以如何合理地设计自己书籍来源的比例结构,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雕版印刷技术是从隋朝就兴盛起来的,这项技术出现不久,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到北宋时,书籍的大量印刷出版,使知识再也不能被官家和少数士大夫所垄断,富商巨贾甚至很多有收藏癖的书生,都拥有大量藏书。
苏轼曾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在他看来,书这种东西实在是太过美妙,不仅有审美价值,还有无穷的使用价值,别的东西要么是外表光鲜而不实用,要么是一旦使用也就使物品发生了折损和残缺(“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唯独书籍是“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可是,坐拥书山而不读,书的“适于用”的价值就不得显现,书籍也就成了只具观赏价值的摆设。苏轼在回顾了印刷技术改变生活的历史之后,大发慨叹: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为什么今人站在众多巨人的肩膀上,理当做出倍胜先人的学术成就,事实却相反呢?“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有书而不读”,苏轼在一千年前的困惑,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更加放大了。
第九,买借要得当。书籍既然是商品,一味地买,一方面容易浪费资财,不经济;另方面也正如“书非借不能读”所暗指的现象,束之高阁以致成叶公之患。
故此,应将“读书藏书比”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有点类似于增长理论中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平衡路径的增长率”。不过,这种稳态增长率不能追求“I=S”(投资等于储蓄),藏书与读书拉开一定档次、保持一定的“赤字”、温和的“通胀”是必要的和有益处的。藏书总是多于读书可以保持一定的前瞻性,鞭策、激励自己持续地阅读,当然赤字也不要太多,否则你习以为常反倒没有动力了。 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于买,什么样的书适合于借呢?
我的建议是,经典书可以买,新书可以借。现在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常常是购买很多各类高数习题集、考证热的各种辅导教材、四六级模拟试卷等等,而且同主题要进很多本,往往就是这些书,被学生借去后在上面涂改、当做了个人的练习册。出现了这种人为导致的破损现象后,还要每年举办主题展览教育学生要爱惜图书。可是,为什么不反思一下,这难道不是图书馆自身也存在问题吗?为什么要大量买进这类书呢?

图书馆(不仅是大学图书馆,还有城市中的各类图书馆)这样的机构,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财大气粗的图书馆来替代个人所不能承担的选择风险,应当是其分内之事。具体说,经典书经历了长时段历史的检验,一本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书,今天还不断有人推荐、出版,从概率上看必有其道理。一本新书,则还有待于这样的检验,特别是当购买者一时不具备鉴赏其优劣的能力时。但是很可能这本新书又确实与你的研究领域相关,这可真是鸡肋。所以,这需要图书馆对图书增量部分作结构调整,及时、快速地购买新书以待读者借阅,并根据借阅数量进行后续调整和淘汰,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经典书特别是专业领域的必备书、案头书,花钱购置就不会有很大的风险。新书更新频度太快,而很多并不具真正价值,所以学术经典的魅力永存。西西弗斯般地、夸父追日般地跟踪新书(当然这里的新书不是指新出版的经典书),吾未见其明也。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角度是,信息时代、移动互联时代的阅读,应该充分用好、用活纸质书以外的各类信息化载体。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手机阅读app软件,也有将整个期刊和藏书数据库纳入移动互联网的移动图书馆平台。这为我们在乘坐公交、地铁之类的细碎时间里,能够更为便捷的阅读(甚至从“看着读”到“听着读”)创造了条件。对于一些专题性的书籍、年代版本久远的书籍,可能图书馆借阅都不甚方便,购买更是没有门路,那么不妨利用上述平台下载到手机、PAD、KINDLE等工具上进行数字化阅读和研究。

有句成语叫“喜新厌旧”,在求知这个问题上,恐怕既要“喜新”,又要“恋旧”或“念旧”。所谓“恋旧”、“念旧”,指的就是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是理论的基石和研究的起点。所谓“喜新”,指的是要进行创新,必然要对新的现象、问题、特征保持好奇,对于对这些新事物的新研究保持高度关注,这是灵感和创造的源泉。这些新东西,经典里未必能够直接提供,就需要到本学科权威和前沿的学术期刊里去阅读、找寻。所以,要做好学问,一要买经典、读经典,二要借期刊、读期刊,三要借新书、看新书。
第十,功夫在诗外。以前读书的时候,遇到数学模型为主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喜欢琢磨其“诗外的功夫”。数学模型是为经济思想服务的,尤记得Romer的《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有一道习题是典型“大而全”、且有着鲜明指向和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它把两种社会保障机制分别设了5问,表面看是在考察柯布—道格拉斯式和对数效用的戴蒙德模型的掌握和理解,实质上目的在于说明基于个体本位决策的分散均衡——“自负盈亏”的优势——不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扰动,在于论证政府强行再分配——通过税收和立法把资本从一个阶层、一个世代手中强行征收转移给另一个阶层和世代的政策对于一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这是全盘推演之后恍然大悟的总结论。
其实很多别具匠心也好,“险恶用心”也好,“包藏祸心”也好,都是“功夫在诗外”的,不足为外人道也。那需要我们借助数学模型但还要超越模型本身去领悟其背后的意思。毕竟,公式是书本上写出来的,而社会和生活却是活生生的个体创造出来的,绷紧这根神经,就不至于陷入某种僵局。
原标题:与大一新生谈读书
【作者简介】
曹东勃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