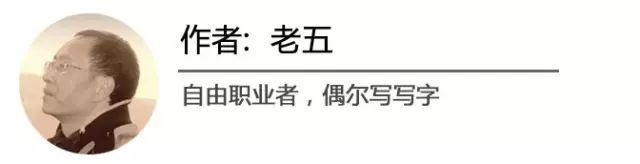《欢乐颂》剧照
她浑身直打哆嗦,脚上的鞋子已经裂胶,右脚大脚趾处还破了个洞,一进屋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学校要求每个人都要买两套校服,他们不给我买,说哥哥坐牢了,要不停地打钱进去,才不会被里面的人欺负,以后出来了还要花很多钱。”
大姐夫妻俩是我家族里唯一重男轻女的一对。他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冉武是老大,女儿燕子虽然是小了五岁的妹妹,却一直充当着姐姐的角色。
亲戚们都觉得大姐一家偏心,亏待了燕子,但大姐从不这样认为。她总能脖子一梗,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哪里偏心了?当妈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娃儿的?儿子女儿我都是一样的。”
大家便举出很多不容辩驳的例子,比如好吃的好衣服从来都只紧着儿子,做事却总使唤女儿,大姐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问题,还有一套自己的说辞:“冉武正在长身体,肯定得吃好点。男孩子要是身体不好,以后咋个养家糊口呢?女孩子嘛,娇小点也无所谓,长得五大三粗还不好嫁!男孩子以后是主外的,哪能一天到晚做家务?女孩子本来就得手脚勤快,才不会被婆家嫌弃。”
老母亲很无奈,也很自责:“都怪我,当初实在是太苦了,没让她多读点书,早早的就回来帮着干活,照顾弟弟妹妹。要不然,她不会嫁得那么偏,还有这种‘封建思想’。”
1995年夏天,我送老母亲去大姐家住几天。那时候,冉武13岁,燕子8岁。
到大姐家时,已经接近中午了,燕子一个人在厨房里煮猪食。听到我们的声音,她钻出来,手上握着一个与她瘦小身板极不相称的大锅铲,欢喜地和我们打招呼,还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脸上立即留下几道黑印。她看了看手,有些不好意思,在裤腿上蹭了几下,又抬起手臂,重新擦了擦脸,结果越擦越黑。
我有些怜惜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他们呢?”
“爸妈干活还没回来,哥哥在睡觉,爸妈说不要吵他。”我和老母亲对视一眼,都皱起了眉头。她陪燕子去了厨房,我径直去了冉武的房间。只见冉武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大姐家唯一的一台吊扇就安在他的小房间里。我黑着脸,一巴掌打下去,“几点了,还在睡?你是大爷啊,要不要把饭也给你送到嘴里去?”
他睁眼要发火,看见是我才爬起来,伸了个懒腰。他光着脚,不情不愿地走出房门,嘴里还嘀咕着:“热死了,好饿啊。”
大姐夫妻俩回来了,我招呼在厨房里烧火的燕子出来,“走,带小舅买包烟,让你哥烧火去。”
“他一个小孩子,会干啥呢?耍你们的,不用他来。”大姐立马高声拒绝。
我拉着燕子去屋后的水槽边洗手洗脸。这才看到,除了十个指甲缝里的黑色污垢外,燕子的左手食指上有几道或深或浅的疤痕。
“怎么弄的,痛吗?”我心疼地问。她摇摇头,羞涩地笑:“好了就不痛了。”她把食指凑到我面前,指着那些疤痕说,“这一条是割麦子弄的,这一条是宰猪草弄的,这一条好像是切菜弄的。”
我带她去村头的小卖部,让她选点自己爱吃的东西。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怯怯地问我:“小舅,我可以买个冰糕吗?”
“可以啊,想吃什么随便拿,我不告诉你爸妈。”她两眼放光,很兴奋地选了半天,才拿了个5毛钱一袋的,叫七个小矮人,里面有红橙黄绿青蓝白,七个颜色迥异的小冰棍。
我指了指那些包装看上去要好一些的雪糕,让她买点贵的。她笑得眉眼弯弯:“就这个,我听同学说这个可好吃了,我还从来没吃过呢。”回去的路上,看着她心满意足又小心翼翼一口一口舔冰棍的小模样,我有些心酸,掏出20块钱给她,“你自己放好,别让他们知道了,想吃的时候就买来吃。”
她一个劲儿地摇头,小脸蛋涨得通红,最后实在拗不过我,才把钱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低着头轻声说:“谢谢小舅。”
吃完午饭,走的时候,我没管住嘴,对大姐说:“冉武不是小皇帝,燕子也不是你们家的使唤丫头,一碗水大体上总得要端平吧。这样惯着冉武,对他没好处。”大姐沉下脸,嗔怪道,“小武懂事着呢,好得很,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事实上,除了大姐夫妻俩,全家就没人觉得冉武懂事。好吃懒做、张口就是脏话,还逃课打架,一身臭毛病。
冉武15岁那年,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偷别人家水果。不仅偷,还故意砍断了很多枝丫,进行毁灭性地破坏。正巧被主人家撞见,主人家气急败坏,一声吆喝,周围的邻居都跑了过来。
他们想逃,最终谁也没逃掉。在各家父母赶来认领之前,主人家把几个人吊起来痛打了一顿,打得几个人全部哭爹喊娘,连连告饶。
见儿子被打了,大姐夫妻俩第一时间做的不是反思孩子为什么被打,日后到底应该如何教育,而是又哭又闹,冲上去就要和主人家拼命,甚至在事后专门跑回娘家,要我们帮着一起去给冉武讨公道。
大家纷纷劝导大姐引以为戒,好好管教一下冉武。结果大姐竟然边哭边说,“我晓得我是泼出去的水,我嫁得不好,穷,你们看不起。人家冉家人一大家子都来了,都见不得自家人被欺负。就你们,个个都请不动,巴不得他被打。哪个男娃娃小时候不费神(调皮好动),他不就是摘了几个烂水果嘛,你们就都把他当小偷看……”
老母亲听得不好受,让我去送她,我心里憋着一团火:“不去,她现在哪里听得进去。非要等她儿子惹出大事了,她才会醒悟。”
● ● ●
果然,初中毕业后,冉武死活就不再愿意读书。夫妻俩四处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师傅,学修电器。他们琢磨着用不了几年,冉武就能出师。有门手艺,也能彻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可惜冉武并没有在他们设想的轨道上安分地走下去,很快就和一群小混混称兄道弟,净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终于,在刚满18岁那年,他就给自己献了一份成人礼——因入室抢劫和故意伤人罪被抓。夫妻俩发动所有亲戚,想找关系尽可能地减低刑罚,可亲戚们在这件事上的积极性都不高。因为在此之前,冉武就已经因为偷盗进了两次少管所了。
最终,冉武被判了6年。大姐哭得昏天暗地,大姐夫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声不吭。
那一年,燕子才13岁,刚上初一。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天都快黑了,燕子忽然敲开我家的门。大姐家离我家几十里,孩子没钱坐车,这么远的路竟然是自己徒步跑来的,所幸路上遇到一个好心的司机,送了她一程。
她大汗淋漓,浑身直打哆嗦,脚上的鞋子已经裂胶,右脚大脚趾处还破了个洞。刚进屋,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学校要求每个人都要买两套校服,他们不给我买,说哥哥坐牢了,要不停地打钱进去,才不会被里面的人欺负,以后出来了还要花很多钱。所以,钱要给哥哥攒着,让我将就哥哥以前的校服穿。衣服又大又旧,上面还有好多墨水印,和现在的校服也不一样……”
孩子说个不停,还委屈地问老母亲:“外婆,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咋就那么偏心呢?他们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喜欢我?”
老母亲回答得很艰难:“不会,他们还是心疼你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一样!”燕子哭得很绝望,“我是手背,哥哥是手心。”
老母亲竟无言以对。一个才13岁的女孩,到底要经历多少来自亲生父母的伤害,才能有如此疼痛的领悟?
第二天,我就带着燕子回去兴师问罪。经过市里时,专门带她买了两套衣服,两双鞋。想着差不多是小女孩发育的年龄了,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好多问,给了她几百块钱,让她以备不时之需。
到了大姐家,我冷着脸,把买校服的钱塞给大姐夫:“她一个女孩子,没有校服,你们就不担心她被同学嘲笑?”
他讪讪地解释,不是不给她买,确实是家里现在没钱。再说了,小武那衣服好好的,哪里不能穿了?她自己假得很,非要学别人,小小年纪就挑三拣四,和人攀比。
我正要发飙,大姐却满脸怒气,拔高了声音说,“这个死女子,这么小就晓得到处告状了,是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来骂我们对她不好,她才高兴呢?我哪点对她不好了,我供她吃,供她喝,供她读书,哪点对不起她了?”
我瞬间就没了和他们争辩的力气。我抬头看燕子,她在不远处背对着我们,蹲在地上宰猪草,每一刀都很用力,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哭。
走的时候,燕子出门送我,一路沉默。我想了很久,安慰她:“因为你哥进去了,他们心情不好,你就当没听见。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就好了。”
她“嗯”了一声,重重地点头,始终没抬头,似乎在使劲地往回憋眼泪。
燕子最终还是没能考上大学,她读完高一就跟着几个小姐妹去了广州,用别人的身份证进了一家电子厂。
她打电话给我们报平安,我有些生气,忍不住责备了几句。她沉默了很久,才说:“小舅,反正我成绩也不好,考不上大学,家里又穷,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出来还自由一些,免得成天被爸妈骂。”
对于燕子打工这事,大姐夫妻俩大力支持,唯一的要求是每月的工资必须寄回来,美其名曰是帮燕子存着,免得她年纪小,花钱大手大脚,或者上当受骗,把钱花完了。
2005年,冉武提前出狱,燕子也18岁了。
接到宝贝儿子,夫妻俩喜笑颜开,似乎日子一下就有了盼头。也许他们是想让燕子回来团聚,也许是担心燕子大了,离得太远不好管,几次三番打电话,硬是让燕子回来找工作,说兄妹俩离得近一点,相互也有照应。
老家不过是个勉强算得上四线的小城市,不像广州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燕子回来后,无厂可进,好在肯吃苦,当服务员、卖菜卖水果什么都愿意干,卯足了劲儿一直在赚钱。
可是冉武看不上这些“小钱”,不停地向家里要钱,说是在和朋友做生意,夫妻俩深信不疑。于是,一笔又一笔的血汗钱砸了进去,却一个水花都没开出来。
次数多了,儿子要的金额越来越大,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夫妻俩才开始质疑。眼看一向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父母居然也会和自己拧着干,冉武暴跳如雷,在家里大吵大闹,疯狂打砸。夫妻俩人又惊又怒。
争斗的结果当然是冉武赢了,武器是一瓶“百草枯”。几次吵闹没要到钱后,冉武翻出一瓶“百草枯”除草剂,双眼猩红,“你们到底给不给?不给,老子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大姐夫气血上涌,难得对儿子硬气了一把:“那你死嘛。”冉武一把拧开瓶盖,仰头就是几口,夫妻俩当场就溃不成军了。都说百草枯无解药,必死无疑。可是洗胃后,冉武硬是没事。医生私下里说,按照他那个喝法,怎么也得有几十毫升,那么大的量还救得过来,多半是假药。
从此,冉武扣住了夫妻俩的命门,但凡再有什么得不到满足的要求,他就威胁要喝“百草枯”。此招一出,总能大获全胜。我们对冉武这种做法很是不齿,一再劝说夫妻俩,“不能再妥协了,这就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狠下心,说不定还能有生机。”
“万一把他逼急了,他又寻了短路咋办呢?是钱重要,还是儿子重要?”两人泪眼婆娑地说。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提醒燕子尽量自己存点钱,同时告诫大姐:“不管怎么样,别动燕子的钱。”
燕子提出想自己管钱,大姐夫勃然大怒,大姐则撒泼打滚,“你啥子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你连自己父母都不相信,还能相信哪个?”夫妻俩把十八般武艺都使了出来。“等你结婚了,我们一分都不稀罕,全部都给你。”
燕子无奈,在和父母的战役中,她从来没赢过。
2009年,燕子22岁,自己谈了个男友,想结婚了。男孩老实本分,对燕子极好,但家里穷。夫妻俩死活不同意,说燕子嫁过去会吃苦,得找个更好的婆家。
僵持不下时,冉武又回来要钱了。这一次,张口就是10万,说是谈了个靠谱的工程,一本万利,稳赚不赔。大姐是真的拿不出钱了,算着燕子这些年上缴的钱,也早被挥霍得一干二净。冉武逼他们,他们就逼燕子,“要结婚也可以,拿10万彩礼。”按当时村子里的行情,10万是狮子大开口。
接到燕子的求援,我们都赶了过去,想说服夫妻俩。见我们都站在了燕子那边,他俩大发雷霆,厉声责骂燕子不孝顺,歇斯底里地和我们争论:“她的钱是被用完了,那又咋呢?我们生她养她,难道不能用她的钱吗?小武坐过牢,又没手艺,现在有机会赚钱,她就那么一个哥哥,她不该帮吗?她就是见不得小武好,良心都被狗吃了。嫁女要彩礼是天经地义的事,她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就朝往拐了。不把钱拿来,就休想把人娶走。”
听着两人不可理喻的言论,老母亲气得浑身发抖,胸膛剧烈起伏,啪啪啪地猛拍了几下桌子,打断了两人的胡搅蛮缠。捂着胸口平息了好一阵,一辈子知书达理的老母亲才颤颤巍巍地指着大姐,喊了声她的小名,声音中满是心痛与失望,“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们要怎么贴补儿子,我们没意见,但你们别把燕子拉进去呀。为了个不争气的儿子,你这是要把女儿往绝路上逼啊。”老母亲话还没说完,气就喘不上来了。
燕子最终还是给了钱,代价是从此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大姐又开始给我们打电话,痛斥燕子居然为了区区10万就和他们断了关系,还要我们都不准去参加她的婚礼。但燕子结婚那天,虽然下着大雨,我们还是都去了,包括大病初愈的老母亲。
那10万,原本是男方家想给他们在镇上买套小房子用的。被掏空后,只得先在农村老家布置新房。因为时间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拉了些新鲜木头铺在地上,勉强遮住了下面的泥土。
在简陋的婚房里,燕子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从小他们就偏心,长大了还是偏心。我16岁就到处打工,他们从来没问过我累不累,做得开不开心,每次都是要我交钱,要我节约,要我孝顺。到现在买东西,我都习惯先看价钱,哪怕兜里的钱买得起,也舍不得,就算是买把菜,也忍不住要从市场的这头一直问到那头,挑最便宜的买。我一分一分地抠,他们就大把大把地给儿子用,从来不为我考虑。他们根本不管这样做,老公家人会怎么看我,我以后怎么生活?到底是我狠心,还是他们狠心……”
老母亲也落泪了,安慰燕子说,“大喜的日子,不哭,都过去了。他们鬼迷心窍,听不进人话,不怪你。断了好,就当花钱买了个清净,以后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就算有人嚼舌根,说些闲言碎语,你也莫放心上,大不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
拿着10万块钱做着“大生意”,冉武确实风光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开了辆小车,载着新交的女朋友和大姐夫妻俩来到家里,说订了家高档酒店,非要请我们这些长辈去聚餐。四姐在外地,二姐、三哥借口有事懒得去,老母亲坐在客厅里,半躺在沙发上,晃了眼冉武脖子上拇指粗的黄金链子,不咸不淡地回绝了,“哎,人老了,再高档的东西也咬不动了,不如家里吃得舒服。”大姐夫妻俩有些尴尬,只一个劲地夸冉武现在懂事出息了。
冉武也是豪气冲天的模样,说自己又谈了几个大生意,接下来准备办公司买房子。最后,他用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口吻说:“虽然燕子不懂事,为了一点小钱就说出不认爸妈和我这个哥的话,但我还是挂着她。他们两口子在菜市场摆摊卖菜,那点小买卖,能挣几个钱?等我把公司开起来了,还是带她一起做生意。”
一直都没啥回应的老母亲连忙摆了摆手说:“别,断了就断了。有多大本事端多大的饭碗,他们两口子,过点小日子挺好。”
果然,2010年底,冉武出事了。大姐哭天抢地给我们打电话借钱,说冉武正在医院抢救。
冉武的钱亏完了,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孩要分手,冉武又对女孩搬出了“百草枯”。可女孩很干脆,转身就走了,他进了抢救室。
这一次,冉武没那么幸运。“百草枯”侵蚀了他的口腔、食道、肺叶、肝脏、肾脏、肌肉。真正面临死亡时,他彻底怂了,毕竟他从来就不是真心求死。他胡乱抓着大姐夫妻俩,全身都在抖,朝自己的父母求救:“你们救救我啊,找医生救我啊,转院啊,去大医院,用最好的药,我不想死啊!”
在洗胃、补液、吸氧、血液灌流等一系列治疗措施轮番上阵后,冉武拖了6天,死得很痛苦。
他经历了从百般哀求到暴跳如雷,到躺在床上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说不了话,只能用眼睛、表情来传递不甘、后悔、惊恐、绝望的情绪。到最后,因为肺部严重受损无法呼吸,他只能像一个被活埋的人一样,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最终被活活憋死。
冉武死了,大姐夫妻俩崩溃了。消沉了很久以后,夫妻俩开始后悔,并且想挽回和燕子的关系,让我们帮着说好话。我们开不了口。
开春后,燕子带着孩子来我家,电视里正好在放《唐山大地震》。有个镜头,姐姐和弟弟同时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姐姐带着对生的渴望一直敲打石头,却听到妈妈喊出了“救弟弟”,看到这里,燕子匆匆起身,去了卫生间。
回来时,她眼睛有些泛红。“小舅,他们来找过我几次。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我真对他们亲不起来了。”她停顿了一下,苦笑道,“说实话,我确实不想看到他们。看一次,就会难过一次,会想起以前的事。我和老公商量过了,准备出去打工。以后,逢年过节,我会给他们一些钱,但是,不会在一起生活了。”
编辑:董俊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