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女子在头发上的装饰,贫富之间,云泥之别。大家女子用浮夸的步摇,光影闪烁间,有团暖和的富贵气象;贫穷女儿家有根头绳绑住青丝,临水照人,亦有别样风情。
在这其中,红发带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杨白劳惶恐躲债回家的路上,还不忘给女儿扯上三尺红头绳,为的是年末的那点喜气——大红袄配红头绳,是乡村常见的审美。
https://res.wx.qq.com/mmbizwap/z ... sprite.2x26f1f1.png);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webkit-background-size: 37px; background-size: 37px;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0px 0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 北风吹彭丽媛 - 中国名歌
北风吹彭丽媛 - 中国名歌
喜儿的红头绳,放在作家萧红身上,便不一定好看。

△《黄金时代》剧照
说她不适合红头绳的,是鲁迅。一次,萧红要去参加宴会,她来到鲁迅家里,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米色、绿色还有桃红色的发带一堆,许广平选了一根桃红色发带系在萧红的头发上说:“好看吧!多漂亮!”又拉着萧红给鲁迅看,她觉得这样的萧红是美丽的。然而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装饰她……’”鲁迅对萧红的服装指导,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鲁迅告诉你,天秤座就是有品味,不服来辩!
许多人揣测萧红和鲁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那么一点小小的情愫,这样怀疑,似乎是有理由的。萧红去世之后,许广平写了篇《追忆萧红》,文中竟有许多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
女人之间,总是敏感的吧,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许广平也觉得,没有什么好顾忌的,“顺便提到”,也许是“憋了好久”的代名词。
萧红对于鲁迅,无疑是有爱的,但这种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觉得并不是那种男女之情,而是一种女儿对父爱的渴望。在鲁迅身边,她每每能够把身体中最天真的一面激发出来,所以她见他,能够“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她为什么笑,她说:
“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这是萧红一辈子,都在等的东西。
她在等爱,也在等爱的人,一直如此,从生到死。

(一)
说起汪恩甲,萧红的第一个男人,人们都会鄙夷而不屑。在《黄金时代》里,他也只有一点戏份,像极了电视剧里一亮相就会被打死的龙套,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周星驰,即使得到一个面目惊恐的小特写,却瞬间领了便当,脸上挂的彩,亦不堪的,仿佛贴了三个字的纸条在上面:“窝囊废”。
汪恩甲和萧红的亲事,是由萧红的六叔张廷献提起的。和电影《黄金时代》里呈现的不同,在介绍这门亲事的时候,萧红并没有提出反对,主要原因是这位未婚夫——长得挺帅。
他只比萧红大两岁,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最初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同班的几个好友都记得萧红为汪恩甲织毛衣的事,织毛衣是旧时女子表达爱意的最高规格,可见两人确实在认真交往。
后来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看起来,这门亲事很相配。
1930年夏天,萧红初中毕业,汪家觉得可以完婚了。喜欢读书的萧红却不满足,她想要继续读书,尤其希望能够去北平读书。7月,在得到家里给她的办嫁妆的钱款后,萧红先到服装店里做了一件新大衣,随后就同陆哲舜结伴去了北平,陆是已婚男子,有人便猜测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却更倾向于认为,萧红当时出走的目的,极为简单——她要读书。在感情上,我认为萧红没有背叛汪恩甲,因为,1931年春节,萧红回家过年之后再次逃往北平,同行的是汪恩甲。根据萧红好友李洁吾回忆,一天他去陆哲舜处,不巧人没在家,就到萧红屋里聊天等待。此时敲门进来一男子,萧红见了很窘,就向李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汪恩甲坐下后并不说话,挺不自然地掏出几个铜板来反复摆弄,屋子里只有铜板敲击的声音,十分尴尬。
在北平期间的萧红和汪恩甲,像许多对即将结婚的小夫妻,采买结婚用品,筹办婚事,许多人以为,这出闹剧很快就会结束,回到家乡,结婚生子,他们不过和其他人一样。
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曾为弟弟婚事牵线的汪家大哥汪大澄,他听说萧红曾经和别的男人出走北京,便恼怒地要求弟弟立即退婚,这件事让萧红的父亲极为难堪——他原是要头脸的乡绅贤达,本又负责城中的风化教育。
萧红便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新娘子把媒人告上了法院。
开庭那天,除了萧红的两个同学到庭助威,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和几位亲属也在场。在法庭上,法官问汪恩甲本案的最核心问题:
“是你大哥逼迫你退婚吗?”
汪恩甲回答:“是。”
这个回答,据说是被逼的,汪恩甲需要顾全大哥的声誉。但这个回答,便让萧红陷入到了绝境,两家的关系也一刀两断。

△萧红
萧红成了呼兰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弟弟妹妹们都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的父亲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没多久,萧红再一次“闯祸”了。她替佃户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大怒,把她痛打一顿后锁了起来,又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
这桥段类似张爱玲的遭遇,看来民国的女作家们都有此劫。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
20岁的萧红逃到了哈尔滨,然后,找到她背叛过,也背叛过她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许多人对萧红的选择表示不能理解,可是,我们站在萧红的立场,只身逃亡的她,这时除了汪恩甲,还能找到第二个保护者吗?更何况,两个人以前还有织毛衣的情分呢!更更何况,所有见过汪恩甲的人都说,他!是!个!帅!哥!
住在旅馆里,每天都会花钱,两家切断了经济援助,于是只能赊账。1932年春,萧红和汪恩甲欠下了600多百元的食宿费,住所也被换成了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
1932年6月到8月,那是萧红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月,阴雨连绵,没有一天出过阳光。有一天中午,汪恩甲说,他出去弄点钱回来还债,然后一去不返。
萧红去找过他,汪家人把她拦在门口,她没能见到汪恩甲,再也没有见到。她默默又回到旅馆,正如她在《乞儿》中所写的那样:“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许广平对于萧红的这种境遇,做了最恰当的比方:“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侯,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
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二)
一开始,萧军对萧红没有什么意思。萧红写信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部求救时,编辑们都商量着要救她,只有萧军是冷漠的。
萧军觉得这种营救方法,没什么用处。“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地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
萧军被派作代表去安慰萧红,他把书交给萧红,转身便想离去,这时,萧红说:“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以后,萧红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萧军一边不经意地听着,一边看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看到这首诗,萧军动心了。
一句话,一首诗,两个人,就这么相爱了。
临走时,萧军留下了口袋里仅有的5角钱,让萧红买点吃的东西。这仅有的5角钱,是萧军的车钱,看完萧红之后,萧军步行了约十里路回家。他时常来看她,但对于她拖欠旅馆的六百多元钱,始终没有办法凑齐。
哈尔滨的大雨给萧红想了个办法。8月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洪水淹没,“水发到二楼了,萧红的房子是二楼,坐在窗台上就可以摸着水。看她的人都跑了,逃命了,就给了她一个逃命的机会。”
房客们乘坐小船,纷纷逃离时,只有萧红还依然在等着萧军的到来。但当萧军游到东兴顺旅馆时,却发现旅馆里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萧耘回忆道:“实在等不来了,她就搭了一条柴船,正好从她的窗口过。
他们爱情中最壮丽的,便是这一刻。

△萧军和萧红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她没有喂这个孩子一口奶,送给了道里公园的看门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音讯。
他们来到上海,在鲁迅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生活。鲁迅为他们设下宴席,介绍了许多文坛的朋友。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对他的感情,这时候,他们郎情妾意。

△《黄金时代》剧照
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她。
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是在青岛吧,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
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为了缓解冲突,动身去了日本,在渡海途中,萧红给萧军写信:“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她再次开始了等待,等待爱的归来,然而没有。
远在日本,萧红总给萧军写信,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这样的事无巨细,在我们看来,是情深意重,但在萧军看来,有点厌倦,他在青岛出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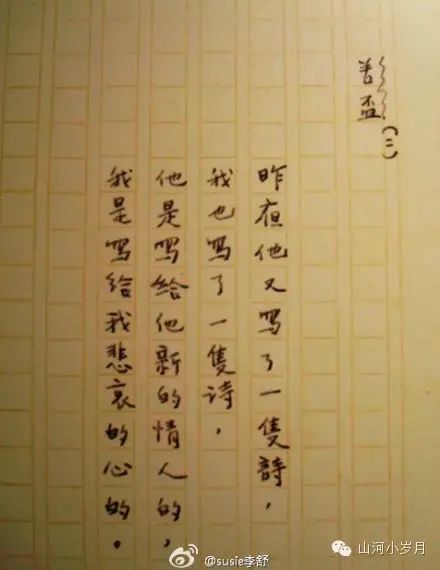
△萧红写给萧军的信
回到上海,萧红继续挨打。胡风夫人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这年冬她回来了……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

△1934年,萧红在青岛
1937年4月27日,萧红去了北京,想用距离挽救感情。她先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住在李洁吾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她给他写信:“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
几天后,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中,萧军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
后来,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日军向临汾进攻,萧军一心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文化人的岗位应当是用笔为抗日呐喊。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萧军说:“我们还是各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若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萧红忍着泪水回答:“好吧。”
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在延安。萧红身边站着端木,萧军以为,只要他招招手,萧红就会回来,但这次,是永别了。
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三郎,我们分手吧。
他们再也没见面。
(三)
好多人骂端木蕻良,我却觉得,端木太委屈了。
在武汉举行婚礼的时候,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他是个温柔的人,他给了她所有可以给的,名分,一个家——这些别人从没有给过。他的家人都反对,可他坚持。
可是萧红觉得他没有。她要一个刚猛的男性,端木没有。
比如萧红、端木和萧军在延安见面,端木虽然不失礼貌地和萧军拥抱,却偷偷地跟聂绀弩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忙啊。”他不敢上前。
可是他还是温柔地对待着萧红,尽管萧红肚子里怀着萧军的孩子。

△端木和萧红
大家指责端木的心理,类似于一对神仙眷侣,忽然分开,正在唏嘘之际,女方忽然和另一人结婚,于是大家便觉得,是那个人,拆散了这对神仙眷侣。
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少么?
另一件事,是有关端木没有照顾萧红。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1942年1月,香港沦陷,萧红滞留在医院里,临死前,陪伴她的,不是萧军,不是端木,而是仰慕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虽然骆宾基是我爱的黄轩演的,但我还是要为端木说点公道话。端木当时在时代书店主持《时代文学》,骆宾基给他写信求助,爱才的端木将自己正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抽下来,换上骆宾基刚写的长篇小说《人与大地》。

△你们相信吗?当年在电影院里,就是这个镜头,我爱上了小轩轩
萧红生病时,端木在外面有许多事情要做,守在萧红病床边的时间可能没有骆宾基多,但照顾萧红的责任主要还是端木承担的。从1941年12月9日至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的45天中,在日军炮火紧逼之下,萧红的住处转移了6次,医院转移了4次,其中包括最有名的罗士达酒店(今天的半岛酒店)、最大的私人医院养和医院、公立医院玛丽医院、法国医院等,这要端木去筹钱、托人、找朋友才行,靠骆宾基是绝对无法办到的。
所以说骆宾基在书中暗示端木在这些天丢下萧红不管的说法,分明不实。
在日军一步一步将半岛酒店、玛丽医院、法国医院军管之后,端木万般无奈才将萧红转移到法国医院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的救护站,萧红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究竟谁说的是真相,已经无从得知。但萧红在死前,确实也曾经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她和端木,也终究没有见面。

(四)
我买了《萧军延安日记》,迫不及待翻到1942年4月8日,那一天,萧军得知了萧红的死。我以为能看见刻骨铭心的悲恸,结果上面记着:“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王德芬,萧军后来的妻子。
顺便一记,萧军还曾经和丁玲暧昧过。再顺便一记,萧军还曾经和一个女大学生生了一个女儿。
端木收藏了萧红的一缕青丝,萧红去世18年之后,他和钟耀群结婚。
端木、萧军和骆宾基打了一辈子的仗,主要为的是萧红的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