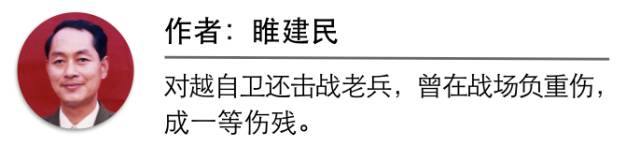网络图
网络图
“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死囚,居然敢在党报上公开抨击时政,这就是不讲政治。”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从国企被分流出来,在我家门口租了临街铺面,卖种子菜籽。生意很红火,没多久,便找自己的未来妹夫做帮手,开车往乡下送货。妹夫是县城附近村子的,我听着名字总觉得耳熟,便打听了一句:“你跟大国和小国是啥关系?”
大国和小国是那村子的亲叔伯弟兄俩,当年因犯抢劫罪被执行死刑时,我就在现场。
朋友的妹夫咧嘴苦笑一下,低头沉默不语。
朋友的妹妹在一旁插话:“他不好意思说,那天夜里,不是他爹撵上夯他一棍,恐怕他早都冇命了。
1996年,我曾应县法院的邀请做些宣传工作,工作是调阅已审结的案卷,撰写新闻稿件。
这年夏季,在全国“集中打击车匪路霸”的专项行动中,县里一个家族式洗劫公共汽车的团伙落网,涉案近20人。其中有一家三兄弟,年龄最大的24岁,小的还未成年。
这个家族团伙所在的村,曾因曹操诛杀吕伯奢全家而出名。据《三国志》载,曹操刺杀董卓未遂,单骑落荒而逃,夜宿鳌头吕村。吕伯奢念及与曹父的旧情,令家人杀猪款待。风声鹤唳的曹操闻听院内磨刀霍霍,怀疑有人要加害他,挥剑将吕家灭门。
再往后,这个村子能称得上是“大事”的,也就是这起当年惊动了国家公安部的团伙抢劫案了。
团伙成员几乎都是本村的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作案则都是流窜到外地。那时,妹夫还不满20岁,眼看着昔日的伙伴聚众吃喝,花钱大手大脚,很是羡慕。于是就趁夜深偷偷跑出家门,想跟那些孩子混在一起,可很快就被他父亲发现了,耿直的庄稼人不会用言语教育孩子,见了儿子掂起棍棒满大街追赶,一棍子将不听话的儿子夯翻在地拉回家。
妹夫被父亲扯回了家,团伙里的大国却把自己的父亲活活气得喝农药死了,自此更加肆无忌惮。
他带领一帮子小兄弟夜宿邻县小旅店,第二天搭乘早班长途客车,拿刀子硬逼乘客掏钱。倘若被洗劫对象稍有不从,就会遭到他们凶狠的殴打。
这场面我还曾亲历过。
一天傍晚,我和堂弟一块去张家口,从县城乘长途汽车到郑州,车行在半道,就见一帮年轻人站路中间拦截。两人持刀拦住车头,司机吓得不敢吭声,另外几个人挥刀子砍甘蔗一样,骂骂咧咧地登上车厢,开始对乘客动手动脚。
车上一名穿军装的志愿兵,站起来就冲歹徒大声断喝:“你们想干什么?”
就在这帮歹徒愣神之际,那军人一个箭步跳下车,挥手冲拦截车头的俩小子连声喝道:“让开!让开!”
军人的威严起到了震慑作用,满车乘客也纷纷起身谴责,歹徒灰溜溜跳下车逃跑了。
那一年正赶上严打高潮,上级有令,对这一系列恶性案件快审快判,从重处理。
虽然这起团伙抢劫案得到的赃款,全部加起来每人平均也不足5000元,却是跨省连续作案,且专挑无反抗能力的民众下手。
有一次,这帮年轻人流窜到安徽省一个小山村,对一位留守的老太太实施抢劫,案值才100多元钱。
没多久,这群年轻人就全部被抓获了。涉案的4名主犯均被核准死刑,年龄最小的一个才20岁,是家里的独苗。
为了保住这棵独苗不死,孩子的父亲挨门磕头,央求全村人在一张白纸上签字画押,由村干部拿着摁满红手印的担保书,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担保书一直夹在卷宗里,看得人心里五味杂陈。
1996年8月14日清晨,我接到法院办公室主任打来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往法院,乘坐院长的警务车去监狱提犯人。
按照政法委的安排,从监狱提出死刑犯,刑车要沿县城闹市街道游街示众,然后到电影院召开“公审公判大会”,之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早晨6点,我和法院院长一起乘车赶到西郊监狱,看见持枪的刑警正从铁门内往外提犯人,为首主犯正是大国,刚剃过的光头泛着青茬,大热天穿着厚厚的夹克衫和长筒裤子,通身崭新的衣服连一点褶都没有。
我身旁站立的狱警指着大国调侃说:“这货好像有预感,这几天早晨起来,天天喊叫着要衣服穿。到前半晌眼见没动静了,又嚷嚷着要脱衣服。”
那年头,监狱内没有降温设施,三伏天闷热,已经被宣判了的死刑犯,通身被脱光,赤条条只穿着裤头,戴上脚镣手铐,由犯人重点看护。
大国从铁门内趟着脚镣出来,昂着头连声说:“嘿嘿,俺是主犯,俺是主犯。”
刑警队的教导员是我一块当兵参战的老战友,我们俩正在一辆刑车旁说话,大国转脸瞧见我们,昂着头冲我战友大声呼喊道:“伙计,你中啊!这回弄住俺哥们,你该升官发财啦!”
几个月前,正是我这位战友带人到外地,根据线索剥茧抽丝,最终破获了此案,并将窝藏在外地的大国兄弟抓捕归案。
战友转头冲大国笑笑。
听说我想去现场,还要采访采访他们,战友连忙拦住我说:“你可不要过去,这帮人都是亡命之徒,啥也不会说的。”
我没再说话。
● ● ●
铁门内提出的第二个死刑犯就是小国,大国的亲叔伯兄弟。
小国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三角裤头,胖嘟嘟满身横肉,出门骂骂咧咧说:“日他祖奶奶,俺这算个球啊,弄5000块钱都够着枪毙啦?那些贪官弄了多少钱,咋不挨枪子啊?”
此刻,小国脚上趟的大镣呼啦响,彷如旧时代的江洋大盗慷慨赴死,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日他姐,再过20年,老子俺还是一条好汉大爷!”
大国看着自己的兄弟小国和另外两个人,浑身只穿一件三角裤头被提出监舍,站在空地上嘲笑道:“咋弄的呀兄弟,看看这窝囊相,咋一点预感都冇?”
包括大国、小国和一个名字叫根的年轻人在内,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表现得都还算正常,惟独那个被全村人担保的独苗苗,脸色蜡黄,脚步像灌了铅水一般,沉重得迈不开步子,几乎是被武警拖出来的。
4个死刑犯依次被去掉脚镣手铐,用尼龙绳重新捆绑住手和脚,面朝西跪在地上,由公检法人员轮流拍照。
拍摄头一张照片时,大国跪在地上,咧着本来就歪的嘴说:“甭慌,俺这最后一张相片,咋着也得照好。”
可大国说这番话时,脸颊的肌肉一直不自然地抽搐着,努力强装出来的笑比哭还难看。
拉死刑犯的刑车,都是临时租用来的绿色康明斯大卡,每辆车载一名死刑犯,站立于车厢前端,由两名持枪武警和几名武装警察押解。
刑车前布置了几辆警车,一路拉响警笛开道。
车队临出监狱大门,法院院长对我说:“你想到现场采访,就坐头一辆吧,可以直接到刑场近距离观看。”
于是,我与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一块,登上了拉大国的头一辆康明斯大卡的驾驶室。
很快,几乎所有的警车,都在同一时刻鸣起了刺耳的警笛,快速驶出监狱大门,向闹市区奔去。
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因嫌闷热,就摇下了车窗玻璃,很快就听见路边一个女人凄厉喊了一声:“哥啊!”
我探头望去,只见路边那个身穿白衣服的姑娘,将一个光肚蔫婴儿高举在头顶,撒腿哭喊着追赶刑车。
刑车上的大国听见了呼唤,扭头看着光肚娃娃吱吱哇哇地乱弹腾,在车上一阵骚动,随即就被两名武警按住头踹倒在车厢内。我赶忙又关了窗户。
刑车一路呼啸,沿着县城闹市街道游行,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拥挤在道路两旁,到处都有人冲刑车上的死刑犯指指戳戳,窃窃私语。
刑车终于在电影院门前停下来,4名死刑犯被快速押下车,从一侧的通道内进入电影院前台,跪在台子上接受最后一道审判程序。
原本通风就差的电影院内座无虚席,闷热的气浪中搅合着汗酸味儿,如蒸笼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上身穿着短袖衫,汗流浃背坐在最前排的观众席。公检法司的各位领导按照职务依次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面色冷峻。
审判员面对着麦克风开始宣读判决书,高声读到主犯大国的名字时,两名武警立即从两边伸手抓住大国的肩头,下边抬脚同时踹向大国的腿肚子,失去重心的大国两腿一软,扑通跪在硬邦邦的台子上,呲牙咧嘴唏嘘一声,昂起头颅两只眼球突暴,凶巴巴地直盯着观众席,很快被武警按住了脑袋。
4名死刑犯被宣判之后,紧接着宣判这个抢劫团伙的十几名成员,一个个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分别判处5至7年有期徒刑。
此刻,那近乎千篇一律的判决书显得是那样冗长,让人听得心烦。
我清楚地看到台子上那个叫根的死刑犯,通身被厚厚的新衣服罩裹着,浓眉毛上往下直流淌汗水。直摇头叹息说:“哎呀,快点吧,快点吧。”
人到了这一刻,谁不想在这世上多待一会儿。而他,却想早点来个一了百了。
上午11点钟,审判会结束了,我依旧坐在头一辆刑车里。车队出了县城沿着去郑州的省道往西奔去。至于刑场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
刑车行至县域收费站东侧,突然熄火停靠在路边。持枪警察迅速下车,将公路从东西实施戒严,禁止所有机动车辆通行。
我下了车,站在路边透气,忽然发现公路北侧有一处黄土岗,岗坡陡峭大约3层楼高。岗下是一处较为平坦的土坑,稀疏冒出几丛杂草,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半死不活。
持枪武警将4名死刑犯押下车,拖进土坑内,面朝北边的土岗一字跪下。
还是依程序拍照,快门的咔嚓声清晰可闻。整个刑场静悄悄的,空气仿佛在一瞬间凝滞了,知了单调乏味的鸣叫声从岗顶的刺槐上传来,让人听得心烦。
路旁站着一位身着中校军服的武警,听说是从市里专程赶来的支队参谋长,从口袋内掏出4发子弹,分发给4名佩戴上士军衔的主枪手,紧接着便喊起口令:“验枪、装子弹、枪上膛、关保险。”哗啦啦的响声整齐划一,熟练的过程不超过一分钟。
正午的阳光直射头顶,暴晒得人头皮发麻,热汗顺着脸颊往下流淌。
忽然,我身旁一阵骚乱,公安局副局长转头冲着一帮女人大声呵斥:“你们干什么?往后退!”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火化厂的几名女殡葬工,手上戴着塑胶手套,拎着塑料袋在现场等着收尸。那几年,县里火化厂效益差,男职工大都停薪下海经商了,只剩下女馆长带领一帮子女职工坚守岗位。
行刑时刻到了,4名主枪手平端着已上膛的冲锋枪跳进土坑内,枪口依次对准死刑犯的后脑勺。
这时候,跪在最西边的大国,突然扭头冲东边的3名死刑犯说:“咱都记住,今儿个是七月初一,咱哥们到那边又够一桌了。”
我眼瞅着大国,屏声敛气,耳际只听一声口令:“放!”
“砰”地一声,4支枪同时开火,现场就听到一声响。4个死刑犯一头栽倒在地,身体像蚂虾一样痉挛着抽搐几下,使劲儿一蹬腿就趴地上不动了。
公检法人员再次跳入土坑内,对死刑犯进行验尸拍照。一张张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脸呈现在面前,我一阵心悸,急忙闭上了眼睛。
就在我愣神的工夫,拥挤在路边的女殡葬工跳入坑内,俩人抬一具血淋淋的尸体,往大塑料袋内装,扎住口迅速撤离了刑场。
之前呵斥女殡葬工的公安局副局长,还在一旁感叹:“我的天哪,这些娘们真胆大!”
● ● ●
后记
从刑场归来,我满脑子都是血肉模糊的场景,那稿子最终也没写成。
我没写成的现场新闻,却有人当了“替罪羊”。消防队一位现役军官是个笔杆子,根据现场见闻,写了一篇通讯,送给县里,被主审编辑编发在四版头题位置。文章中引用了小国走出监狱时说的那句话:“那些贪官弄了多少钱,咋不挨枪子啊?”县委书记看了大发雷霆:“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死囚,居然敢在党报上公开抨击时政,这就是不讲政治。”
书记一怒之下,那位主审编辑就丢了饭碗。
我亦有收获,刑场之后,我写了一篇名为《殡仪馆里的铁娘子》的通讯,发表在国家级报纸上。那个女馆长还因此荣获了全市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而刑场的见闻,我直到今天才写下来。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