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坦布尔,飞屋环游记系列
2016春节长假连载
图·文︱刘德科
壹︱First
在看了1593次之后,他买下了那栋房子。
他是一位疯狂的买家。那是贫民窟里的旧房子,完全不匹配他的富二代身份。
只因那栋房子里,住过他爱的人。
这是小说里虚构的一栋房子,但你却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它,在伊斯坦布尔。
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是先有房子再有小说,还是相反。
那部小说叫做《纯真博物馆》,你大概已经读过。那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最伟大的作品,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写完。
小说最后几页附录里的那张地图,煞有介事地标注了纯真博物馆的地址。帕慕克还在题为“幸福”的最后一节中,印了一张参观门票。
很多人以为地图和门票只是小说家的故弄玄虚,其实那都是真的。
写完小说后,帕慕克仍不过瘾,他决定按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建一座真实的“纯真博物馆”。
我根据小说附录中的那张地图,找到了那栋房子。

纯真博物馆后院
贰︱Second
还是简要地介绍一下发生在《纯真博物馆》里的美妙故事。
30岁的伊斯坦布尔富家公子凯末尔在婚礼前,突然爱上了出身贫寒的远房表妹,刚满18岁的芙颂。在一段短暂的疯狂爱恋之后,芙颂突然消失了。
饱受思念之苦的凯末尔,解除了原有的婚约。339天后,凯末尔终于找到了芙颂,但她已经嫁人。
凯末尔便以亲戚的身份,频频造访他的远房姑父姑母——芙颂的父母;其实他是为了去看望芙颂,虽然她和她的丈夫也住在一起。这种状态一共维系了七年零十个月:“其间一共是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
最后,芙颂终于决定离婚。
她终于要和凯末尔结婚,却在前往巴黎旅行的途中遭遇车祸。芙颂因此去世。幸存的凯末尔,买下了芙颂一家住的那栋房子,把它改建成一座“纯真博物馆”。它的全部藏品,都是凯末尔在过去悉心收集的关于芙颂的一切——她爱过的和她碰触过的一切。
对于这个伊斯坦布尔的爱情故事,你完全可以像看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那样充满期待,但吸引的你并不会是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细致入微的记忆。
你也不必恐惧会看到《追忆似水流年》那样无聊的联翩浮想,那不过是法国作家惯于炫耀的小说技巧。我想说的是,《纯真博物馆》去除了经典文学著作惯有的阅读障碍,它值得拥有更多读者。
与其说它是一本爱情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伊斯坦布尔的断代城市史,写尽了这座城市的建筑、服饰、汽车、餐饮、电影、礼仪、城市化进程以及政治变革。

去芙颂家要经过的塔克西姆广场
叁︱Third
我的伊斯坦布尔之旅,纯粹是受了《纯真博物馆》的诱惑。
我常常跟自己玩这样一个游戏:突然记起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就要在书中找到它,看看到底在第几页,看看到底要花掉我几分钟时间。
这部几十万字的小说,让我大概读了几十遍。
没有读过《纯真博物馆》的人不会明了,我们是怎样染上了凯末尔式的鬼迷心窍。
在凯末尔去芙颂家吃晚饭的七年零十个月里,他一共收集了芙颂抽过的4213个烟头。
纯真博物馆里真的就陈列着那些烟头:每一个烟头下面,都注明了他拿到它的日期;每一个烟头的形状,都是芙颂掐灭它时的心理状态。
一切藏品,都是芙颂所爱过或接触过的,也是芙颂被凯末尔深爱过的证据:发夹、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
一切都太真实了。以至于许多人只能不停写信向作者询问:“帕慕克先生,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帕慕克先生,凯末尔就是你吗?”
帕慕克只好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回答小说与现实的各种纠缠方式。
据说,为了建造现实中那座纯真博物馆,他几乎耗尽了小说带来的巨额版税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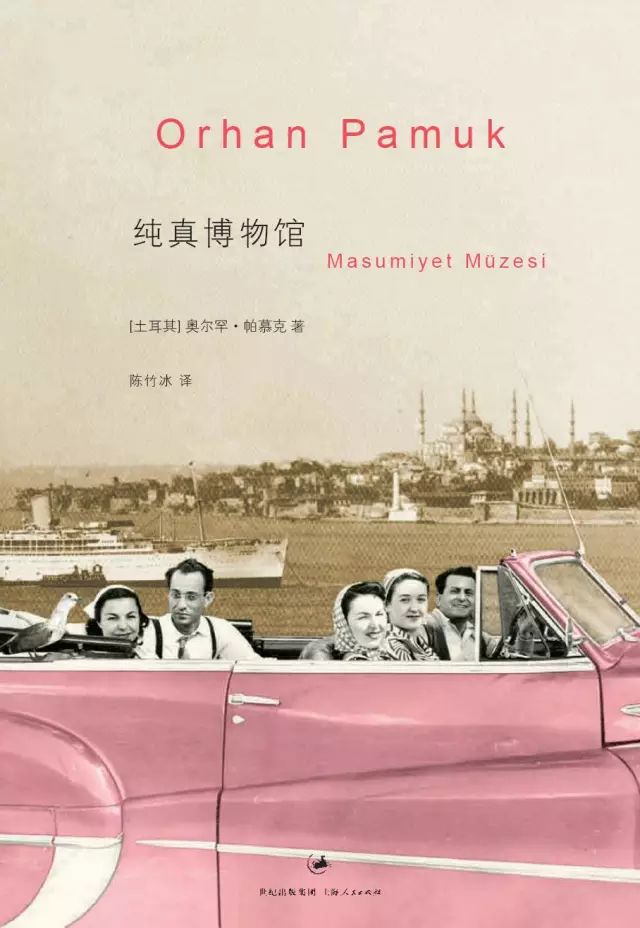
《纯真博物馆》中文版封面
肆︱Fourth
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偶遇一株迎风绽放的向日葵,请记得多看几眼。
帕慕克这么描述凯末尔与芙颂44次性爱中的第一次,在小说第9节:“她整个身体都在轻轻地颤抖”,“请你们想一下向日葵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微微颤抖的样子”……
在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纯真博物馆》的性爱描写可以排名第一。
我喜欢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找寻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在帕慕克家族公寓附近,一家叫做“Armanggan”的土耳其本土品牌,它的旗舰店营业面积超过了这里的任何一家世界大牌奢侈品店。它用自己独有的浅杏黄色金子,制作出了像蕾丝一样复杂的金丝饰品。我细致入微地参观了这间高达六层的珠宝店,幻想着在灯光璀璨的橱柜中,遇见一对镶刻着字母F的耳坠。
纯真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就是一对镶刻着字母F的耳坠。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结束之后,芙颂把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落在了凯末尔的床单上。
无论你是不是《纯真博物馆》的读者,应该都不会厌恶我在这里抄录这部小说无以伦比的开篇第一段——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做爱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天际线
伍︱Fifth
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终其一生都未曾踏上过伊斯坦布尔的土地,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年迈之时写下著名的诗篇——《驶向拜占庭》。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那时的伊斯坦布尔被称为“君士坦丁堡”。
叶芝说,在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治下的拜占庭帝国,艺术摆脱了物质与情欲的束缚,成为灵魂的歌唱。
帕慕克的著作几乎不曾触及充满历史神话意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蓝色清真寺,他把更多笔触留给了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他创造了伊斯坦布尔的当代神话,用富家公子凯末尔和他的远房表妹芙颂,取代了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伦、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了拜占庭首都,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成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
倘若没有帕慕克,很多人恐怕更愿意把伊斯坦布尔叫做“君士坦丁堡”。
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而言,那些名胜古迹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只是为了给帕慕克小说留一个美妙的注脚。
在傍晚时分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海面上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穹顶和蓝色清真寺高耸的听音塔,在玫瑰色的天空与橘红色的夕光中,成为一帧黑色的剪影。这时候你大概就会明白,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为什么总是“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2006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奥尔罕·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蓝色清真寺,伊斯坦布尔
陆︱Sixth
忧伤,是伊斯坦布尔现代神话的惟一主题。帕慕克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伊斯坦布尔,把它们集合起来,便是卷帙浩荡的伊斯坦布尔城市史。
忧伤是《黑书》中的律师卡利普想要进入妻子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边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攀藤玫瑰;
忧伤是《新人生》中的一个建筑系男学生从广告招牌、海报、闪烁的霓虹灯、药店展示窗、烤肉店及彩票商店的名字搜集字母,拼出恋人嘉娜的名字;
忧伤是《杰夫代特先生》中的商人杰夫代特羞愧地吻了一下泽内普女士的手,在做这个动作时,他仿佛想起了儿时的一些记忆,几件家具、一只小虫子和一块绣花桌布;
忧伤是《寂静的房子》中百科全书作者的妻子法蒂玛拿了颗樱桃,放进嘴里,就像是颗巨大的红宝石一样,在嘴里含了一会儿,然后咬了一口,慢慢地咀嚼着,等待着水果汁和味道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
忧伤是《纯真博物馆》中富家公子凯末尔在修理厂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看到他的恋人芙颂遭遇车祸时的那辆1956式雪佛兰车骸时,瞬间因为百感交集感到了一阵晕眩;
忧伤是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扉页上留下了一句“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许多人的伊斯坦布尔之旅,大概都是受到帕慕克小说的诱惑。不为人知的是,帕慕克也曾受到类似的诱惑:“我三十岁时第一次去巴黎,那时我已经看完了所有重要的法国小说,我跑到那些在书中遇到的地方。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主人公拉斯蒂涅那样,我来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高处,俯瞰巴黎市貌……”